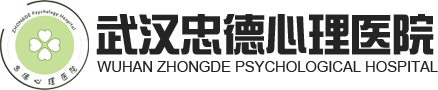电影《Lars and the real girl》(国内译名《充气娃娃之恋》)讲述了一个因为小时候经历养育创伤而变得无法跟人建立关系、离群索居的男主人公拉斯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国内译名叫《充气娃娃之恋》,《充气娃娃之恋》的译名容易让人联想这是一个关于宅男如何沉醉于他的幻想世界的故事,其实这只是主人公故事的起点,全片是讲述主人公拉斯如何从这个起点走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阶段,海报上的诠释“The search for true love begins outside the box(对真爱的找寻始于盒子之外)”是点睛之笔,拉斯在是借由盒子内的娃娃打开了盒子外的真实世界。英文片名《Lars and the real girl》可以直译为“拉斯和真实女孩”,如果中文片名采用直译的话有一种双关性,“the real girl”其实既可以指代他买的人偶,也可以指代最终拉斯走向的那个真实女孩——玛戈。

影片开始,拉斯裹着一条围巾(妈妈的遗物)站在屋内隔着紧闭的窗户看着外面的世界,一位女士来邀请他吃早饭,拉斯拒绝了。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拉斯拒绝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怀孕的嫂子凯琳。对亲人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拉斯更是保持着警惕和距离。然而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同事对他提起定制人偶,没想到拉斯在六周后真的买了这样一个定制人偶比安卡,并在精心梳洗打扮后隆重地把她介绍给了哥哥格斯和嫂子凯琳。

哥哥格斯一开始觉得拉斯一定是疯了,要看精神科医生,嫂子凯琳虽然也是大为诧异,不过还是保持了冷静,稳住了拉斯,两人决定把拉斯和比安卡一起带着去见家庭医生,同时她也是心理学家。他们想根据医生的看法再做决定。柏曼医生是第一个接受拉斯主观性想象世界的人,她并没有当着拉斯的面指出他的妄想和荒诞,而是愿意更多借由比安卡来了解拉斯,在确认拉斯的社会功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之后,她建议格斯和卡琳接受比安卡的存在。虽然很困难,但凯琳和格斯还是在他们能力范围帮助他们自己以及社区的人来接受比安卡,而善良的社区居民们确实慢慢接受了拉斯,并进一步让比安卡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她是一个真的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一样。

电影展现了拉斯在兄嫂、社区的帮助下逐渐打开内心,更多融入社会环境的过程。在影片的叙述中,透过拉斯与心理学家的交谈,我们也了解到拉斯的一些早年背景,他的妈妈是在生他的难产中去世,之后爸爸带着两个孩子,看起来爸爸因为妻子的离世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可能是一个抑郁状态,而大一点的格斯也受困于一个迷茫的状态中,所以在格斯有能力离开家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家,留下爸爸和拉斯在一起生活,等格斯再回到家乡的时候,拉斯已经独自住在车库了……
温尼科特作为精神分析师与儿科医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提出了他关于客体关系的理论,相较于克莱因重视的潜意识幻想和投射认同等心理防御机制,他更多的强调了环境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主体是如何借助于一个抱持性的环境来发展出他自己的自体身份感。
温尼科特认为婴儿在诞生之初是脆弱而无助的,他们没有随着遗传而来的原初自我力量,所以必须绝对依靠一个养育者(主要是母亲)来辅助婴儿存活下来,并且这种存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性喂养和照顾,还包括着心理性的存活以及随后获得自体身份的合法存在感,真正启动朝向整合的生命历程。这种心理的成熟发展需要在出生头一年里由大量母性养育工作打下一系列基础:包括母亲帮助婴儿将躯体安住于精神之内,获得时间和空间的整合感受,满足婴儿从幻想到与现实的链接需求(即从适应到去适应的过程)等。
温尼科特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与别人的关系,从一个独立个体到进入与他人的二元关系是需要一个坚实基础的,这种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个体生命成熟度逐渐提升的过程,他在《对客体的使用》这篇论文中提到了一个发展的序列:(1) 主体关联到客体 (2)客体进入一个逐渐被发现的过程,而不是被整个主体世界所替代 (3) 主体摧毁客体的过程 (4) 客体在被摧毁攻击中幸存活下来 (5) 主体能够使用和利用客体。

所以温尼科特在谈到客体使用这种能力的时候,他会指出一种叫做客体关联的能力必须在更早阶段得到发展,而这种关联的能力实际上是要借由一个好母亲来给予的,母亲每一次充分响应婴儿的时候,就是一次重要的关联体验。“‘关联的客体’可能是主观性的客体,而‘使用的客体’意味着客体已经变成外部现实的一个部分。”换言之,关联的客体是婴儿在主观幻象领域里和他产生连接的那个客体,婴儿会把自己的感觉投射到这个客体身上,而忽略或者说没有能力去看到这个客体真实的属性,而到了使用客体阶段,这个时候婴儿自己已经发展出了一定的自体身份感,因此他与客体的关系是一种两个有身份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开始真的具有了人际互动的色彩,而这样一个转变发展的过程需要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客体本身能够经得住婴儿的发展性需求的使用,从最开始的作为满足全能体验的服务者到能够通过承受住摧毁性而被逐出婴儿的主观世界,进入客观领域存在并展现出其真实性,从而在二元关系中与对方建立更有爱恨情仇体验的关系。

电影里拉斯和比安卡的生活并不像童话故事大结局一样永久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之间开始有了间隙和冲突。对拉斯而言,比安卡从这样一个最初的主观性客体的存在逐步变为具有独立性存在的对象。当然,比安卡本身并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客体,因此它不可能仅仅只是做为一个物品而发挥对拉斯的疗愈作用,比安卡的功能是以哥嫂、社区的群体支持为一个更大的环境性背景的,是这个环境辅助了比安卡满足着不同阶段里拉斯的心理需求。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拉斯是有给比安卡一个人设的,比安卡的母亲也死于难产,她是由修女养大的,学过护理,借年休机会来认识新世界……这些其实都是拉斯自己的主观想象,他想象着比安卡懂他,愿意和他共处,愿意参与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安卡就像是一个好妈妈一样,无时不刻都在身边,让他感到安心。在这个阶段里拉斯和比安卡是一体的,他们的关系像是没有缝隙一样,完美且完整,借由比安卡,拉斯的安全感和自信感会得到提升,让他有了勇气去参加同事辛迪在家举办的聚会。

当这种客体关联的感觉慢慢发展的时候,比安卡也越来越融入社区生活(也是一种被社区所使用的呈现),她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有很多要和别人相处的时间,这意味着她和拉斯的关系从一种融合的关系里会开始有了距离,这种分离感给拉斯的本能反应是愤怒,他很生气。过去比安卡是在他全能的掌控之中的,是完全属于他的,现在比安卡也部分地被他人使用这件事让他触及到他自己害怕被抛弃的体验。但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可以理解为,拉斯在足够多的安全融合体验中开始可以孵化出他自己了,他有了更清晰的对“我”和“非我”的体验,所以才会对那个“非我”的比安卡不在自己掌控之内感到恼怒。
这就好比一个穷人从来不用担心自己会被盗,只有你有了足够的资产,才会开始为资产要怎么保管怎么升值而担忧。虽然拉斯的体验是别人抢走了比安卡,但也可以理解为是拉斯发展到了一个允许比安卡和他有所不同的位置,就像婴儿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如果他被妈妈养育的足够好,那么他有了一些对世界的基本信任感,他也就可以承受住妈妈不用24小时呆在他身边,妈妈可以晚一点点出现,可以短暂地去忙一点别的事情。拉斯和比安卡之间的客体关联的体验已经足够充分了,所以才为接下来的客体使用进一步打开了空间。

接下来更近一步的发展是拉斯“宣布”了比安卡的病重,这就预示着他对客体的摧毁这一幕内心大戏真的上演了。从个体来讲,对客体的摧毁并不带有敌意攻击的意图,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发展自身的需要。如果说最基础的信任是你对我好,我在你的眼中感到我好,那么更高一层的信任体验是我对你不好,你还对我好,那么我就可以相信我可以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可以不用惧怕因为做真实的自己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发展真自体的重要环节。比安卡的病重和拉斯对玛戈的情感增加是有关联的,这使他产生了冲突,他想要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他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比安卡的病重是化解拉斯内心冲突的解决方式,这意味着他要开始摧毁这个一开始由他自己主观建立起来的形象了,拉斯允许自己卷入现实社会的能力比之前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作为人偶,比安卡自然无法展现出某种主观意志,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拉斯周围的人所给出的反应,他们还是很惊讶,格斯和卡琳再一次找到心理学家柏曼,他们一开始以为这可能是一种和心理治疗有关的设定,但柏曼告诉他们,这都是拉斯自己的安排,是他发现了比安卡的昏迷,是他决定比安卡处于垂危状态。再一次,家人和社群的人又配合着拉斯的需要,他们没有指责拉斯为什么要打破之前的平静,让本来已经融入社群的比安卡淡出视线,他们作为一个延伸的环境承受住了拉斯的这种摧毁性需求,这种承受而非报复给了个体进一步往下发展的空间。
温尼科特在文章中写道:“由于客体幸存下来,主体现在要开始在客体世界中过一种生活,而且因此主体一定会获取不可限量的收益。然而,主体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要接受在无意识中与客体-关联有关的幻想将被持续不断地摧毁。”这种摧毁性的顶峰在拉斯那里是他最终让比安卡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种精神上的死亡,虽然比安卡死了,但是这个死亡也冲破了拦在拉斯与玛戈之间的障碍,拦在拉斯与真实他人关系之间的障碍,他可以不再那么退缩于与人的交往,把他的爱恨情仇更自由地放置到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拉斯是幸运的,虽然他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拥有着的亲人、社群的力量又何尝不是一个好母亲?而在这样一个促进性的环境里,那种朝向整合的倾向,生命的原初创造性让拉斯可以突破自己的冰冻状态,品尝到更多丰富的人生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