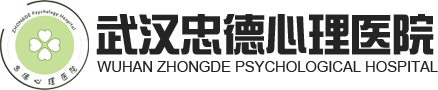马上六一了,突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小书,叫《儿童精神分析五讲》。
为什么叫小书,是因为它其实是一本收录作者埃里克·迪迪耶于2009年在川大做的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五次讲座合集。内容非常有趣生动,埃里克作为一名法国非常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师,并没有用晦涩难懂的术语,而是用非常平实,通俗的语言向听者和读者娓娓道来他所遇到的一个个小个案的故事,以及他在倾听这些故事遭遇中所做的分析性理解和处理。整个阅读过程非常流畅享受,而我的脑海里对埃里克也会有另一个意象——一个诗人,一个孤独流浪的诗人。
埃里克是法国非常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师,所以在临床中会接待大量的小来访者。就像他在书中说到的,很多成人来访者都惊讶地认为给孩子做分析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是如何和那些小不点儿们打交道,排除他们的心理障碍的?而更重要的是,分析师到底是如何做到倾听他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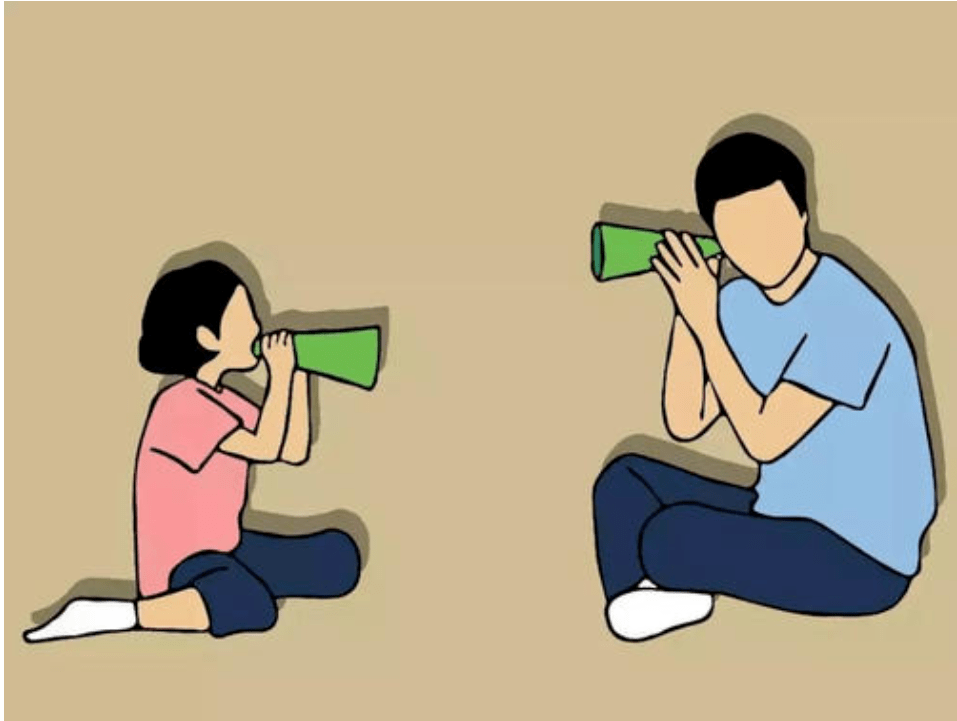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自己曾经难道不也是一个孩子吗?尽管他们可能早已忘记了这件事。而精神分析就正是一个作为唤醒你沉睡已久的内在小孩的场所,让那个无法接近、飘忽不定又难以辨识的孩子醒来,让那个被你遗忘却又让你躁动不安的孩子醒来,让那个曾经被冷落在一边有很多话要倾吐却无人倾听的孩子醒来,让那个无人倾听甚至无法说清自己所承受的痛苦的孩子醒来。
和小来访者进行分析工作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冒险。
孩子们常常被父母带到医院来见我们,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在学校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情绪或者行为的问题。可能是打架、说谎、在课堂上难以集中注意力、违反课堂学校纪律、也可能是他们显得内向、沉默、孤僻,没有同学或小伙伴愿意和他一起玩,甚至还有更加严重的偷盗行为,自我伤害自残的行为。很多第一个发现这些问题的会是老师,他们会建议或催促家长对孩子有更多留意或者管教,但显然大部分父母在孩子的这些问题面前都是束手无策的。
在另一边,在孩子那,又发生了什么呢?似乎好像没人知道。包括孩子自己,可能也不认为自己遇到了问题。孩子们来到咨询室前,他们仅仅只是对无法达到老师和父母的要求而感到无助和无力;亦或是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被老师父母批评、管教无效,最终作为惩罚的另一种形式而被送到你——一个陌生人——的面前。在他们的幻想中,你极可能只是另外一个老师的替身,另一双代替爸爸妈妈监视的眼睛,另一根束缚他们“无稽之谈”的天性的绳索。

所以他们在你面前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忍受着这个陌生环境和对面这个陌生人或是“间谍”的恐惧,忍受着与父母50分钟分离的焦虑。他们用沉默向你表达拒绝和抗议,或者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动作但绝不理会你的任何谈话的邀请。
我们在此刻能做的,仅仅是耐心的与眼前的这个孩子慢慢熟络,与他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与他们的父母建立良性联盟……埃里克在演讲里就提到,他曾经在与一个孩子一年的相处中,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陪着他,而一年后某一天的某一刻,当这个孩子出现一个变化,真正的分析才可能真正开始。
在和孩子一起咨询的工作里,会了解到其背后大量的家庭和学校的情况。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家庭成员组合,有的父母会宠爱、溺爱他们的孩子,把孩子视作国王;有的父母则对孩子漠不关心、冷漠、疏远;还有一些父母无意识里也许并不喜欢小孩,甚至厌恶小孩,他们会无意识地把自身的苦恼和问题压在孩子身上;还有一些父母无意识里不能忍受孩子超越自己,比自己做得好,于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在学校里,似乎老师才有话语权;在家里,父母才是最后定夺者。孩子们要做的就是安静,听话,像其他的小孩一样正常上学,正常考试。显然,我们常常会在话语中阉割了孩子。这让孩子缩回到沉默中,缩回到那个无形的空白里,孩子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在录像里,一个婴儿被他的母亲抱在怀里,他向这位母亲投以热切的目光,娇弱无力的等待着母亲的回应,可这位母亲的眼睛却一直望向其他地方,神情呆滞忧郁,仿佛臂弯里的这个孩子并不存在。婴儿并没有放弃尝试,始终将目光投向他眼前的这个人,但在重复数次这样的无回应后,实验观察发现这个孩子最后不再对身边任何声响及任何触碰做反应,好像他只是在自己的世界中。
想要让他再次对周遭有所反应,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重新与之建立有效的回应和亲密的联系。但在他曾经无数次投以热切目光尝试过程里,在他感受到的那个匮乏和空白的世界里,婴儿们也许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声音——一个朝向他们的声音,以及一个支撑他们的目光。而事实上,当我们作为咨询师在与成人的分析工作里,他们同样像是孩子一样,等待着一个外来的承认的信号,一个欲望的信号。如果没有它,那似乎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很多人用一生在等待这个信号。
孩子是人,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弗洛伊德表示,在我们身体上的某个东西,让我们说了些不可理喻的话,做了些不可理喻的事,与我们本来想说的,本来想做的,背道而驰。
这里的“某个东西”,可以理解为在我们身上表现的症状。“问题小孩”所表现的症状和矛盾,一方面是促使父母将孩子带到咨询师面前的原因,但同时,这些症状和冲突也蕴含着另一层意义,它们给孩子带来了一样好处,即通过某种症状,某种行不通,某种神秘的东西,证明了自己存在着!——我尿床,我在学校里不肯学习,我偷拿小伙伴们的东西,故我存在。对于那些保留症状和冲突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道理之一。
孩子的一切表达,也许都是在观察并理解了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后所作出的反应。他们会看到父母脸上浮现的种种细微表情,父母的所思所感都在顷刻即逝的表情中尽显无遗。他们也会从父母的声音中听出各种不同的语调,懂得他们表达背后的真正用意。因此症状对他们是宝贵的。

很常见的,在成年人的咨询工作中,被分析者虽然拥有看似成人的身体,心理却停留在一个孩子的状态上。他们的超越没有真正地完成。他们总是停在那里,无法从症状的位置去到一个更合适的话语上,也无法从一些让他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壮的男孩或是最美的公主这样的梦里走出来,他们想要伴侣给予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就好像他们仍然需要吸食妈妈的乳汁一样。
但是接受分析的孩子们会超越这种情况。精神分析提供了发展话语的场域。
一次治疗就是一次相遇。他们在与分析师的相遇中建立、支持并强制自己不要待在那个原初场景里。这个话语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谎言,而是在“表述”,表述幼儿要么在场要么缺席的话语。无论这个场景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爱或者多么富有悲剧性,我们必须抓住的是,当这个场景发生的时刻,主体被剥夺了话语。我们要发掘出这个场景,并且在极度的困难下,陪伴他重新访问这个场景。因为只有在事后,在这个场景发生之后,孩子才能自在地得以重生。并在这一次后,孩子才可能重新给出这个场景的评价,这个不在时曾经强加其身的评价。这样,我们重新找到了话语,才能找到孩子究竟在哪儿。
埃里克在书中提到,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过着流浪的生活,因为我们被根本性地剥夺和截掉了两个基本场景:一是我们生命的开始,我们如何被孕育,因为父母赋予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并不在场。第二个场景是我们的死亡。因此,我们对自己的开始和结束都一无所知。
巧的是,精神分析却在这个根本性的不可能中建立了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框架。一个象征的框架,由分析师决定,所有的分析场景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每一次分析时间都有始有终。分析时间长短变化,即便是很微小的变化,都跟我们自己的结束一样,不可预测。跟解析一样,一次分析的终止是对话语的切割,也是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话语的切割。如果没有这些切割,话语就成了无止境的永恒的独白;没有这些切割,我们就会在一个无休止的、乱伦的时间中。
精神分析是一个地点和一段时间,其中给出了被症状所固定的表达和创造的重生机会。精神分析,是对重视、苛求、速度和效率的世界的沉思与冥想的场域。是一个可能的即兴表演的场域。言说即是这场即兴表演的方式,就像我们舞蹈中迈出的第一步,一幅画上落下的第一笔,石上凿出的第一个刻痕:一次次地对抗令我们重如磐石的重力法则及其共谋。
除了言说,别无他法。
最后祝所有小朋友及曾经是小朋友的大朋友们六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