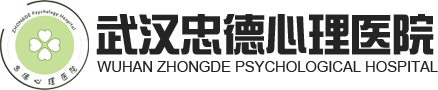否认与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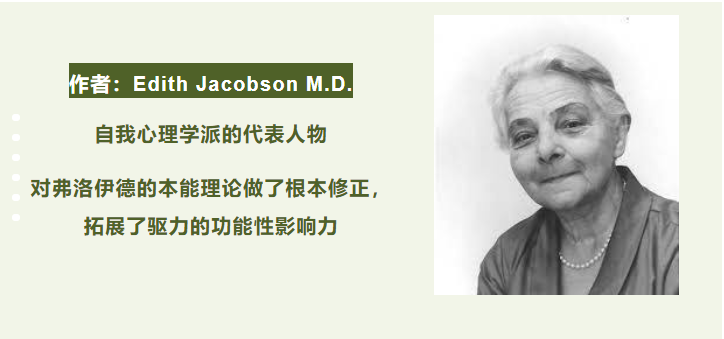
在自我使用的多种多样的防御机制中,我们发现某些机制,如情感隔离、否认、内射、投射,与神经症患者相比,在边缘型或精神病患者中似乎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显然,这类病人需要这种防御,因为自我的压抑能力不足。但这种说法并没有涵盖更为复杂的事实。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病人并没有一种均衡且坚固的压抑屏障,这面屏障应该具有坚实的反精神贯注自我组成物(countercathectic ego formations),能够只允许某些本我的努力(id strivings)和本我的衍生物通过或侵入自我。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只有非常僵硬的反应模式,大部分是强迫性的,但又非常的脆弱。在治疗中,我们观察到这样的病人虽然恐惧地意识到可能的崩溃会导致精神病发作,却仍然固执地依赖这些反应模式。关于他们压抑的本质,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随时准备制造不加掩饰的本我材料的病人,比如有意识的乱伦和同性恋幻想等等,却可能会对最重要的创伤性的童年记忆表现出健忘症,就像一道无法掀开的铁幕。他们有关俄期和前俄期的过去就现在而言是存在的,或者可能记得起来,但是他们与那些深埋的婴儿时期的历史却是完全失联的。
例如,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19岁男孩有时会产生大量的前生殖器期和生殖器期关于乱伦与同性恋的幻想。这个男孩记得一系列小时候与父母和护士在一起时的受伤经历,他会通过反复讲述这些体验来支持他的偏执防御。但他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婴儿期的记忆材料,以便与他当前的幻想建立联系,并用于重建对过去的理解。在进一步的观察中,我在这个病人身上看到,就像其他精神病患者一样,那些露骨的、不断变化的幻想和冲动会随着反向形成防御机制的崩溃而出现; 就像那些当前被用来否认和遮掩其他更具威胁性的幻想一样,实际上它们只是失去联系的本我碎片。例如,在这样的时期里,每当这个男孩被一个年轻女孩激起性欲时,他就会产生明显的乱伦幻想。乱伦幻想掩盖了他通过杀死母亲来摆脱母亲的愿望。还有些其他的时候,绝对被动的有受虐倾向的同性恋诱惑可能激活强奸、刀杀或在街上勒死妇女的冲动。
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病人唤起本我的某些部分,不仅是因为压抑屏障被打破,这些本我的部分也充当正常的自我防御的一种暂时的劣质替代品。一旦达到结构性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和驱力中立化(drive neutralization)都消失的程度,结构性冲突(structural conflicts)就会被那些入侵自我且对立的本能努力们(id strivings)之间的冲突所取代,而这些本能努力可能会交替地被用来相互否定和屏蔽。由于防御性幻想容易再次引起恐慌,因此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幻想变式,这表明患者从一种本能位置(instinctual position)到另一种近乎疯狂的转换。
有时,这些患者的婴儿期与近期的记忆和记忆缺陷似乎是有组织的,并以相似的方式在发挥作用。也可能表现出对整个重要的童年时期的健忘症,却可疑地对其他婴儿阶段拥有清晰的记忆材料。但这些婴儿时期的记忆与神经症患者的记忆有本质上的区别。奇怪的是,它们可能没有被扭曲。例如,性场景或其他事件的细节被精确地记下来。但是他们不是在情感上隔离且撤回的,就是在其他情况下或其他阶段,呈现过度的情感投入并且讲述起来就像今天发生的一样。我们再次感到这些过于清晰的记忆孤岛,虽然没有被结构性的屏蔽掉,但有一种防御功能,他们可以确保那些特别可怕或令人失望的童年事件能够完全被遗忘。例如,虽然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困惑,但他们可能完全无法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度过过去几天的,与此同时却将注意力疯狂地集中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一个幼稚的幻想或类似的事情。重要的是,这奇怪的健忘症并不是选择性地抹掉单一的、痛苦的经历,而是成批地消除。
它们的本质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它们包含了大量的对外部和内部现实的否认机制,这种怀疑在对特定神经症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这些神经症患者偶尔会表现出类似的婴儿健忘症和对当前事件的健忘。但是,与精神病患者相比,他们通常能够恢复被抹去的体验。我要补充的是,潜在的精神病患者越接近一种显性的精神病状态,他们就越容易忽视当前的现实,并过度沉溺于过去或他们认为是过去的东西。这让人想起那些癔病患者,他们那些关于婴儿期诱惑的记忆,其实只是幻想而已。然后他们可能会展示他们所谓的回忆,或者在情感上疯狂的投入,对他们近期的和婴儿期的过去进行怪诞的重建。这些材料被证明是对过去的一种妄想式的扭曲,也就是说,将当前的妄想性幻想的内容重新投射到过去。当然,与癔症不同的是,这类患者往往妄想般的确信他们所假定的回忆是真实的。
在这一点上,我也许可以停止对精神病患者的评论。我想强调的是,鉴于这些令人费解的观察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类病人是无法压抑或压抑不足。他们的防御系统表现出复杂的异常,这对分析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本文仅作为未来对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初步探索。当然,对否认的任何新的观察都是有价值的,包括否认的性质、它与压制不同的运作方式、它与压抑以及与其他防御机制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作用。
当然,使用否认绝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特权。正如克里斯(E. Kris)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否认在正常生活中也能够发挥有价值的作用。对于许多以自恋型人格类型为主的神经症患者来说否认足够作为辅助防御来使用。容易分析的患者当然比精神病患者更适合作为研究这种机制的对象。

二、
我的一些分析案例在防御行动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似乎相当清晰地凸显了否认的特征,我相信,这些特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我选择了这些病人中的一个作为相关病例材料在这里进行简要地介绍。
F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教养、优雅的年轻男性,三十出头,来自西海岸,最近刚结婚。临床上他混合了强迫和抑郁型人格结构,倾向于见诸行动,并在偶发的身心症状和歇斯底里症状间互相转换。尽管患者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足,有时会被他那些强迫且抑郁的抑制(compulsive-depressive inhibitions)妨碍,但他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总的来说,他在任何活动中都缺乏主动性和真正的快感,包括性交。他的主诉是他的感情生活是如此乏味和颓丧。他是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好像总是走在阴暗处,渴望阳光。尽管有这些情感上的干扰,后面我们还会细说,病人能够与他的妻子保持亲密的关系,他的妻子是一个温暖、冲动的女人,她在感情和本能上的高度投入吸引着他。
在移情过程中,他同样发展出一种动人、温和、深情的依恋,这种依恋多年来严格排除了性欲或明显的敌意。他对妻子和分析师的情感显然与他童年时两个重要的人物有关。其中一个是朋友的孤女,比他大十岁;一个温暖且相当诱人的女孩住在他们家里多年。另一个是患者唯一的弟弟,在患者六岁时出生,三岁时死于小儿麻痹症。这个孩子和他同住一个房间。病人对这个小弟弟和他悲惨的疾病与死亡有着最清晰、最深情的记忆。他对弟弟的死感到极度悲伤和沮丧,他希望死的是自己,而不是这个可爱的、惹人疼爱的孩子。他花了好多年才发现自己对这个小入侵者的怨恨,这种怨恨使他在放学后习惯性地跑到朋友那里,因为“家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这位病人和他父亲的关系也非常亲密,直到青春期,他的矛盾心理、叛逆和疏远越来越多。父亲在病人18岁时死于败血症。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出现了严重的惊恐反应,“全身颤抖”几乎到了抽搐的地步。这次发作是在模仿父亲临终那几天的寒战。
父亲死后,家里人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一个情妇身上。但病人不记得自己曾有意识地责怪过父亲的错误行为。恰恰相反,他对父亲的“勇气”感到由衷的钦佩,因为他觉得父亲“有理由”开始这场昂贵的婚外情,以此来解令人讨厌的母亲的毒。他对父亲最好的朋友试图挽救财务危机的行为毫不关心,而是立即怀着极大的解脱感离开母亲去了另一个城市。
这成就了病人与生命中另外两个重要女性的关系:他的母亲和他的情妇,在结婚前,他和情妇生活了6年。病人坚信他从来没有嫉妒过他亲爱的弟弟,他更加坚信他从来没有爱过自己的母亲。他形容她是一个非常美丽,但冷漠、抑郁、不聪明的女人,她总是唠叨他,脸上习惯带着受伤和责备的表情。他从母亲那里只感觉到冰冷的怨恨、恼怒和想要摆脱他这个负担的愿望。当家乡发生地震时,他有意识地、冷血地希望她会遇难。当朋友们说他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儿子时,他充满恶意的回应是,她从开始就是一个更糟糕的母亲。他觉得爱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令他羞耻。但是这位病人完全不记得四岁前的童年时光。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坚称自己从未爱过母亲,这一固执的主张屏蔽并否认了他在前俄期对母亲的深厚依恋,这种依恋在他三岁半时被创伤性地破坏了。
他和情妇的关系是在父亲死后几年发展起来的,在那之前,他和一个长得像母亲的漂亮女孩有过一段令人失望的恋爱经历。那时,病人一直非常抑郁而且总是生病。与他的母亲和初恋情人相比,这个女孩非常聪明,像他父亲一样,在他生病期间慷慨的提供照抚。他转向了她,就像他在童年早期感到被母亲遗弃时转向父亲一样。同样重要的是,她的腿有残疾,这让他想起了弟弟的小儿麻痹症。虽然他从未爱过她,但他钦佩她,需要她的支持,对她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但在得知她秘密堕胎后,他觉得自己必须忠诚于她。他们的关系包括性关系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但他继续和她生活在一起,不愿意结婚,但又不能离开她,她越来越让他想起那个病弱、唠叨、责备的母亲。他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沮丧,最后对情妇像对母亲一样产生了冰冷的怨恨。在与母亲和情妇的关系中,病人在模仿他父亲的同时又反叛父亲,他的父亲在引诱了母亲后感到必须娶她为妻,虽然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是敌对和贬损的,但是从来没有抛弃她。患者就像一个怀着恶意的小男孩一样,也是这么做的。
当病人感到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时,他突然想到,既然他不能抛弃他的情妇,他可以杀死她——例如,用他可以搞到的毒药。这些谋杀的念头还未到偏执的程度。此时,病人甚至没有像责备母亲那样责备他的情妇;他只是觉得,尽管她是有价值的,但他并不爱她,可是拴在一起,他只是想摆脱她。杀死她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任何内疚感。他深信,只要他感到安全,确信不会被抓住,他就不会为犯罪而感到悔恨。
当然,病人并没有执行他的计划。相反,他请教了一位比他年长很多的律师朋友,这位朋友认识且非常欣赏他的情妇,所以力劝他不要分手并与她结婚。于是,病人设法抓住朋友在职业判断上的严重错误,随后,如释重负地也和这个律师朋友决裂了。现在他终于觉得可以离开情妇,并且能够爱上另一个女孩,与她结婚。
我们无法深究那些被朋友间冲突唤醒的他与父亲之间明显的同性恋冲突。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父亲死后他的一系列见诸行动重演了往事。那个虚伪的,曾经宣扬道德,并在形式上恪守道德,却在暗中犯罪的父亲,使病人摆脱了自己对母亲的罪疚感。于是,在揭露朋友之后,他又一次设法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女人为自己开脱,只是这次不是母亲,而是他的情妇。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她虚伪的爱和善良愚弄了。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后,他现在可以认同一个光荣的、充满希望的父亲形象,这个父亲不会偷偷地犯罪,而是会无情地揭露并抛弃母亲,并与另一个女人寻找婚姻的幸福。
他的见诸行动是他的病态超我(superego pathology)的缩影。虽然病人有时会感到严重的抑郁和自我批评,但他很乐意承认自己没有真正的良心,也就是没有一套具有指导性的道德原则。他的生活主要遵照一些特定的显规则,就是他所谓的“适当或不适当的行为”。他认为自己和别人都没有理由对不好的想法感到内疚,只要它们没有被付诸行动。此外,与表面上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会大声疾呼“摆脱虚伪的道德”,捍卫他个人认为任何属于“正当”的行为。因此,冷酷的死亡愿望甚至谋杀的念头可以在一个无法感受到或表达丝毫愤怒、并且总是显得极其正派的人身上存在,而且不伴随任何焦虑或内疚的迹象。
一段五到六岁的童年记忆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他的超我功能异常开辟了道路。病人和他怀孕的母亲在乡下度过了夏天。他回忆起那年夏天的一天,他拿了一根棍子,刺穿了花园里的一只小蟾蜍。大腹便便的蟾蜍与怀孕的母亲联系在了一起。病人想起他无法直视这只受伤的蟾蜍,因为它“用责备的眼光看着自己”。他只是想把它处理掉,"让它消失"。他杀死了这只蟾蜍。越来越清晰的是,无论他做什么来安抚和取悦他的母亲,以及后来的情妇,他们永远都像那只受伤的蟾蜍一样,“用伤害和责备的眼光看着他”。然而,这种无法忍受的、责备的目光使他被这些女人擒住,让他甚至想要像那只蟾蜍一样“让她们消失”。因为抛弃它们就会招致公开的冲突和伤害,所以只有清除这些令人厌恶的物体才能避免受伤。
病人逐渐显现出有意识的内疚感,尤其是对他母亲的内疚感,引发了对俄期和前俄期冲突的分析。一开始,病人不仅否认自己有超我,更否认自己有俄狄浦斯情结。事实上,他不可能真的相信无意识的存在,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别人。他否认超我和本我存在的信念明显地通过他的情感态度表现出来。每当他否认超我时,意识层面的信念也随之消失;当他否认本我时,即没了激情也没了快乐。无论哪种情感体验都是他渴望的,尽管它们可能会让人极度不安,但也证明了一种对“直接”的冲突的向往,一方面是情感和本能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是一种来自内在良心的强烈且确信的声音。
当他梦见自己和母亲还有弟弟比利一起经历了空难,然而这个比利并不是现实中的那个,而是“第二个”比利。弟弟在空难中死亡,而他和母亲活了下来,但她却疯了。当他去疗养院看望她时,对她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爱,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这是病人的分析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梦给病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童年事件。这时,病人突然想起来,他的母亲一定是在他三岁半的时候流产过。“如果这是真的,”他兴奋地说,“我就可以相信潜意识了。”这个梦确实非常接近现实。流产由一场手推车引起的事故造成的:这件事是在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在家里发生的,而在那之后的好几个星期他母亲一直感到身体不适和抑郁。这是造成他和母亲关系破裂的创伤事件。对在童年早期与母亲关系的遗忘,为他否认早期依恋以及母亲的怀孕和流产引起的严重冲突提供了保障。
此外,创伤事件的灾难性影响被否认,并被非常清晰的关于性游戏的记忆所掩盖,在四岁时,一个小女孩邀请他给她手淫。他对她“漂亮”的器官和她强烈的生殖器快感的生动回忆,有力地证明了女性的生殖器是一个强大的器官;的确,比阴茎更漂亮,更有力。这个坚定的信念帮助他否认母亲的生殖伤害,也否认了由此产生的严重的对阉割和内疚的恐惧。
显然,孩子目睹并猜到了大部分的事实。然后他被丢给了女仆,他感到失落和困惑,但是他无法责怪自己正在病中流着血的母亲,也无法指责他此刻绝对依赖的父亲。随后的材料显示,在他的幻想中,他认为这场意外是一次犯罪,凶手正是他的父母,最终是母亲犯下的罪行,但他那体弱、抑郁、爱责备的母亲却好像总是在责怪他。六年后,小比利的死亡再造了早期的创伤。从那时起,病人就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无法接受也无法忍受,因为在他看来,父母才是“真正的罪犯”。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他对情妇的病态反应了。她的秘密流产,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病弱,这使病人的内疚冲突和敌对情绪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谋杀的想法代表了一种终极的、神奇的、防御性的手段,他认为可以使他免受不应有的惩罚。与此同时,他们的目标是报复,惩罚性地消灭“真正的罪犯”。
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使我们对他(过敏性)身心症状和癔症症状有了很多的理解,这些症状反映了他对受伤的或垂死的家人的受虐性认同。
当他达到不再否认的程度后,强烈的愧疚感,然后是怜悯,最后是对母亲的感情被允许出现,并且取代了他的症状。最终,他自己的“内疚感”浮出水面,即他严重的前俄期和俄期的敌对冲突,尤其是隐藏在对父亲的同性恋依恋和对弟弟的母性依恋后面的强烈嫉妒和仇恨。
我们的病例报告就此结束。对于否认的研究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三、
这位病人的核心问题是在他母亲怀孕期间发展出来的,并集中在渴望虐待狂式的攻击母亲子宫的想象。通常情况下,一个孩子可能会通过压抑被禁止的冲动,通过对母亲和婴儿的爱再加上反向形成的防御来保护自己,从而控制对未来对手的恐惧、嫉妒和仇恨。在这个病人身上,命运阻断了这种正常的解决之道。不幸的是,他的施虐欲望得到了满足:首先是母亲的流产、她的疾病、抑郁和遗弃;然后是比利的死,他不顾一切的爱也救不了他。因此,神奇的愿望实现变成了一种惩罚,这是他的施受虐人格发展的萌芽。病人终其一生都摇摆于对惩罚性权力的顺从和对不公正惩罚的敌对反抗之间。他对母亲关爱的需求如此早的就被创伤性地掐灭了,以至于她一直是他敌意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病态的内射和投射的主要目标。由于她曾是如此,她必然会吸收从父亲和弟弟身上转移出来的大部分恐惧和攻击,并轻而易举的就扮演了受害者、凶手和法官、诱惑者(本我)和报复者(超我)的角色。
失去比利后,病人开始承受所有慢性抑郁症的症状。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状态和其他受虐的表现,因为他的目标是避免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该承受的”内疚冲突。为此,他建立了一个强大却无效的魔法防御体系,理应可以保护他免受两方面的伤害:他对内疚的恐惧和内疚本身;隐匿的受虐和自我惩罚的倾向以及更深层次的施虐倾向。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以否认为主要成分的防御机制。我们可以从病人对抗潜意识内疚的斗争开始。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癔症病人受困于一种潜意识的对惩罚的需要。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压抑和情感抑制是有选择的且局限于对特定的禁忌冲动和相应的内疚感,这两者都能在癔症症状中找到有意义的表达。除此以外,癔症患者是冲动的、情感过敏的,而不是压抑的,他们通常受到焦虑的折磨,除了压抑的那个部分,他们了解内疚的痛苦。我们选择这个病人的原因是在他的案例中防御系统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运作。我们的病人不仅成功地避开了针对具体事件的内疚,而且还避开了内疚和焦虑本身,不仅避开了禁忌冲动,而且完全避开了真正的本能冲动。事实上,他的防御机制非常极端,足以一石二鸟:他们同时处理掉超我和本我,彻底到他可以否认其中任何一个的存在。他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
我们认为,患者受困于对感情,思考和行动的普遍抑制。但这必须被详细说明。案例材料表明,他不仅像强迫患者那样,将想法和相对应的情感分离,还笼统将行为、思想和感觉分离开来,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它们。情感上淡化了的邪恶想法是被允许的,只要它们不会变成坏的行为就无法造成任何伤害。但最后,他杀人的念头和抛弃情妇的真实行为也能被充分地合理化和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他的主要目标当然还是全面地抑制情绪,彻底到让他能够逃避任何无法接受的本能驱动的真正情感体验,无论是性的还是攻击性的,以及因此产生的任何焦虑或内疚——总之,所有不受欢迎的和不愉快的感觉。在这个机制的帮助下,他甚至可以让最被禁止的努力浮现到意识中。
但是,为了这样的逃脱,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人生失去了真正的乐趣,生活变得极其乏味和空虚。然而,当不良的感情和冲动产生时,他设法否认它们的真实本质。他有时会显得闷闷不乐,脸上流露出焦虑或内疚的表情,但他不愿承认自己感到沮丧、焦虑或内疚。由于他的死亡愿望是冷酷且无情的,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认它们敌对的本性,并利用它们作为一种魔法防御。他的性行为是如此的强迫,以至于他觉得这是“一项必须做的工作”。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抱有同样的态度,以至于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真正的快乐。
偶尔,他会用相当刻薄的话伤害妻子,但却对自己这样的行为毫无觉察。当他的所作所为被摆在他面前时,他先是想不起来这件事,然后也不明白这些话为什么能够伤到她。最后,他感到十分痛苦,但却会否认自己被自责折磨。他的防御方式让人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人被指控借了邻居的锅,却把锅弄坏了,以至于没有办法还回去,这个人声称(1)自己完整地归还了锅,(2)锅本来就坏了,(3)他就没有借过锅。
就像笑话里说的那样,我们所描述的防御机制目前还不够有效。他的否认需要来自投射机制的进一步支持,投射机制也是彻底处理了本我和超我。他的超我恐惧就这样被外化了,变成了对受伤的女人的恐惧,她们责备的眼神会伤害他。不仅惩罚性的超我,还有内疚本身(本我的努力)都被钉在父母,本质上是女性的形象上。我们记得他揭露了虚伪的权威们,他们假装是好的(理想化自我),但实际上是罪人(本我),却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责而指责他(超我)。他对不道德的赞颂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投射防御,这确实让他成为一个伪君子,因为这意味着在理想化的伪装下被压抑的还是得以回归。
在隔离、否认、内射和投射机制的辅助下,大量的压抑和普遍的抑制的防御相互作用和协作,使他的防御结构到达某种程度,最终能够实现对本我和超我的存在的否认,或者,我更愿意说,直接拒绝为他的本我和超我负责。他对这些心灵系统的否认且拒绝负责,并将他们投射到外部,为他处理问题建立了不同的基础。他现在可以把内心冲突当作与现实的冲突来处理。他可以通过隐忍的姑息或必要时逃离或消除危险客体来避免犯罪和惩罚。这就解释了他见诸行动的倾向,我们经常在使用他这类防御的病人身上发现这种倾向。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见诸行动中有对感知的过度精神贯注。在他的感情和性生活中,注视和被注视扮演了支配性角色。他的性幻想和性行为都与一个主题有关:否认自己的虐待和阉割愿望,揭露女性伴侣的这些努力,以及否认或撤销他们的阉割。例如,在他的幻想中,有攻击性的女人会通过展现出对他阴茎不可抗拒的欲望来引诱他,他会被动地提供给她们使用。在性活动中给女性惊喜的幻想不仅会引起性兴奋,还会带来胜利的喜悦。
和他的妻子,他可以通过持续的努力来取悦她,在性方面满足她,同时放弃自己的性心理需求和生殖器快感,来维持一段相当令人满意的关系。由于他成功地通过制造和观察“她脸上性兴奋的表情”来“让责备的表情消失”(撤销了她的阉割),他觉得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可以回报以感激之情。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就像对待他的母亲和情妇一样,他就会在性和情感上变得怠惰、冷漠、隔离,有时甚至到了人格解体的地步,假装他自己或她不存在。在对这种状态的绝望中,他最终会觉得必须消灭她,以免自己死去。
我对病人的防御性操作的描述旨在将注意力集中在否认的特征上,这体现了它与压抑不同的运作方式。为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应该在脑海中有个印象,专业术语“压抑”(repression),正如弗洛伊德在《潜意识》这篇论文中定义的那样,本质上指的是对驱力或它们的概念表征(ideational representations)的直接防御(同时对相应的情感的抑制)。传统上,这个词被应用得更为广泛,甚至弗洛伊德本人也这么认为。例如,我们所说的“记忆压抑”,不仅指对本能驱力的防御,也指对外部影响事件的遗忘。鉴于否认最初和基本上是针对外部现实的,这一点将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获得重要意义。
事实上,不需要特别精确的术语,因为几十年来,否认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本身几乎未被研究过。弗洛伊德已经在《梦的解析》的第七章中指出:“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事实,这种逃避痛苦的行为——鸵鸟策略——在成年人的正常精神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第600页)。在同一章的最后(第618页),我们发现了今天我们认为是否认的两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弗洛伊德当时仅仅把它们作为前意识和意识之间审查的证据。这与我们稍后将讨论的压抑和否认之间的地形区别(topographical difference)有关。
为了获取目前关于否认更全面的信息,我们最好转向列文(B.D.Lewin)的书《兴高采烈的精神分析》,其中包含了对这种防御及其运作方式的最仔细和巧妙的研究。它包括对亚伯拉罕、多伊奇、A.安吉尔、安娜弗洛伊德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关于否认相关文献的回顾。
列文引用了弗洛伊德对压抑和否认的比较,弗洛伊德至少间接地暗示了这两种防御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他们是在同样的婴儿时期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然而,临床观察毫无疑问地表明,否认是一种比压抑更古老、更原始、更早出现的机制——事实上,它的前身是儿童为了努力摆脱对外界不愉快的感知而使用的防御。正如列文对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大纲》中的评论做总结时说:“否认是对外部世界的否认,就像压抑对本能的否认一样。”因此,从根本上说,否认总是对感知的否认,这可以通过抽离对不想要的感知的精神贯注来实现。列文说,只要否认“可能会协助或取代压抑”,它就可以被用作对抗“内在现实”的防御手段。然而,与压抑和防御相反的是,“他们是直接对抗本能……而否认是为了避免焦虑。”这是一个重要的说法,我们的案例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强调,我的病人主要是为了避免焦虑,往大了说,他是想避免所有不愉快的感觉。
然而,如果否认的目的是避免不愉快的感受,乐观主义者和轻躁症患者毫无疑问的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否认也会否定快乐么?例如,悲观主义者和抑郁症患者,他们毫无疑问地公开地拒绝承认(disclaim)和否认(deny)外部世界的或自身的任何快乐的部分。这里只需思考一个简单的悲观主义者的例子就够了。当然,他总是做最坏的打算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未来的痛苦和伤害。因此,否认令人愉悦的现实似乎仍旨在避免焦虑和痛苦,即使它可能无法达到目的。
当然,所有的防御最终都是为了避免焦虑。但在压抑中,信号焦虑(signal anxiety)激活了一种对抗危险源头即本能驱力的防御性斗争。反观否认,列文说的很对:“当本能表征(instinct representations)进入意识,并要求自我接受它就是现实 (这里指的是‘内部’现实,但也可以被当作外部的)时,否认就会出现。”
事实上,这似乎就是否认的特征,它开始于自我对危险信号的反应,即直接尝试忽略这个信号本身。我倾向于相信,这种即刻的、初始的对危险信号的否认,是为了预防自我开始进行真正的防御斗争。自我所能做的,不是将敌对的驱力驱逐出它的领地,而是否认它们的存在,否认驱力入侵带来的危险、痛苦的影响。
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这些思考是与压抑和否认的差异有关。压抑是将想法置于潜意识,并抑制相应的情感反应,与之相反,否认显然最多只能阻止已经到达前意识的想法进入意识。
就像弗洛伊德前面提到的例子一样,否认似乎是在前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了一种审查制度,或者说是一种保护屏障。这是一种防御,似乎在自我的领域内起作用。这与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恋物癖”的论文和《精神分析大纲》中关于否认的评论是一致的,他在文中谈到了由否认引起的自我的分裂。通过比较压抑和否认,他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发现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或态度。而在压抑的情况下,一方存在于自我中,对立的另一方存在于本我中,在否认的情况下,两方都存在于自我中,从而导致自我的分裂。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是一个地形上的或结构上的区别。
但是弗洛伊德关于否认和自我在否认中的分裂的观点留下了一些尚未解答的疑问。他自己说,他只把恋物癖患者的案例作为一个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引起的自我分裂。除了特殊的冲突解决模式外,恋物癖的基本防御与所有那些为避免女性阉割的可怕想法而在女性身上附加“幻想的阴茎”的男性或女性患者的防御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关于否认的非常好的例子,对女性阉割的否认,阐明了在这种防御中经常会涉及的对现实的扭曲。事实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扭曲了现实:即使女性没有阴茎,她们也肯定没有被阉割。儿童对女性生殖器官的普遍误解确实揭示了本我对最初知觉的直接影响,费雪(C. Fisher)最近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研究 。在这个例子中,对现实的直接而痛苦的扭曲是孩子自己对被阉割的恐惧和愿望的具体的外在反映和确认。我们对否认与压抑进行比较的重点在于,在否认中,自我用对立一方的想法,也就是本我的幻想,来防御那些令人害怕的想法,而在这里本我的幻想成为一种令人渴望的、愉悦的幻想。这个令人愉快的想法同样也可以利用某些感知来证实自己。
总的来说:在本能冲突的影响下,对立双方的想法同时对自我进行精神贯注,并且扭曲对外部现实的感知,由此愉快的、渴望的想法被用来否认那些痛苦恐惧的念头。
这似乎是否认工作的基本方式的特点。列文在提到一个病人时指出,否认是“…一种快乐自我的功能,…体现了自我组织的这种早期类型”(第58页)。比较否认和压抑,我们看到,在压抑中,反精神贯注自我组成物保护了对无法接受的驱力表征的压抑。在否认的情况下,令人渴望的本我幻想倾向于扭曲现实,以此防御一个对立的可怕想法,而这个可怕的想法同样是扭曲了现实的。
这一对比让我想起我最初对精神病患者的理解,他们使用明显的本我努力(id strivings)来防御对立的、更可怕的本我冲动。因此,无论何时使用否认,在自我的领域内结构性的冲突——至少在一个有限的部分——可能被本能的冲突所取代。这意味着,否认倾向于影响思维过程,干扰逻辑思维、对“事实”的认同以及对现实的检验,其程度比压抑要大得多。
然而,临床事实是,在神经症患者中,这些对立的想法通常被实实在在的深深压抑着,也就是被精神贯注到本我中,尽管如此,这些防御性的对具有阴茎的女性的渴望性幻想更接近表面,并会在患者的自我态度、社会行为或性行为中表现出来。但弗洛伊德未完成的论文“自我在防御过程中的分裂”显示弗洛伊德实际上认为这些想法最早出现在最初的婴儿情境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想法代表了对现实感知的原始扭曲和否定所导致的自我分裂,他们可能会在进一步发展中经历一个真正的压抑的过程。我们意识到,否认一词并不总是被用作指代一种正在使用的防御;我们同样可以非常正确地说:一个压抑的想法是对一个对立的、不受欢迎的、同样被压抑的想法的否认。在临床中,我们经常发现,当这些被压抑的想法重新进入意识时,患者可能仍然拒绝接受现实,并再次诉诸否认和扭曲作为最终的防御手段。这个想法将证明相关的讨论的必要性,也更进一步证明否认和抑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婴儿健忘症的发展。否认和扭曲现实的这些想法可能会被压抑,这一事实与否认作为一种防御仅仅只能使一个想法呆在前意识的假设并不矛盾。
通过与压抑的进一步比较,列文表明,“否认可能像压抑一样在双重身份下运作。它可能反对一些对外部事实的理性认知,比如死亡,或者“它可能反对外部事实所带来的情感影响”。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否认甚至可能不会阻止无法接受的想法达到全意识(full consciousness)。但在这种情况下,否认仍然可以避免焦虑和不愉快,要么通过掩盖这些不良想法的真实本质,要么作为一种终极手段,阻止相应情感的痛苦本质被意识化。F先生的案例材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否认使用了所有这些方法。
列文强调,不仅外部现实可以被否认,而且内部现实也可以被否认,然后被视为“外部的”。问题是否认如何能像处理外部现实一样处理内部现实。
我们对孩子否认女性阉割的讨论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第一条线索。我们提出,被阉割的女人和有阴茎的女人的矛盾形象扭曲了现实,是孩子本能冲突和恐惧的具体或近乎具体的表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否认利用外部现实以达到间接反对内部现实的目的。
在F先生身上,对女性阉割的否认也在他防御对阉割和内疚恐惧以及潜在的被禁止的冲动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他的防御堡垒建立在更广阔的土地上。他利用否认作为一种防御手段,不仅可以抵御由外界现实的感知所引发的不愉快的想法和感受,还可以与压抑合作,直接对抗本能的幻想、愿望和冲动。显然,我们现在要试图解决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尽管否认不能有效地抵御本能,那么这种防御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能够直接对抗内在现实也就是所谓的本能驱力本身呢?
我们记得,最初,孩子不能区分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即他不能区分令人沮丧或愉悦的体验是来自于对客体的感知,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内部体验。如果否认处理精神表现(psychic manifestations)就好像它们是某种外在现实一样,那么否定内在世界的前提必须是部分的退行;不是退回到最早的阶段,而是到一种“具象化(concretistic)”的婴儿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虽然已经意识到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区别,意识到自我和客体的区别,但仍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它们。
我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说内在现实的“外化”是正确的,至少在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完全混淆或等同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例如,如果小约翰尼在发脾气后向他的妈妈保证,现在坏的约翰尼已经走了,好的约翰尼又回来了,他完全知道他是对谁生气,现在又是对谁重新感受到爱。但是他仍然用具象化的、人格化的和概括的术语,即坏的消失和好的约翰尼重新出现,来体验和表达他的思想和感情、他自己的状态和行为的变化。这个小约翰尼的例子当然会让人想起我们的案例。
我认为,我们的病人同样无法体会、鉴别和区分具体的哪些是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感觉或想法、哪些是幻想或冲动。尽管他通常不会喊口号,但他倾向于使用“攻击”、“性”、“爱”、“良心”、“激情”等术语来概括这些心理表征,仿佛它们是自我的某些具体的部分一样,或出现或消失,他们是他缺乏或已经失去的,也可能是他想要发现的,恢复的和拥有的。这概括了我想要提出的观点:这种否认是以一种幼稚的精神现实具象化为前提的,这种具象化允许使用这种防御的人把他们自己的精神反抗(psychic strivings)当作那些可以感知到的具体客体一样来对待。此外,这些人也倾向于以同样具象化的方式对待他人的精神表现。例如,我们的病人并没有真诚地回应一个女人的愤怒或受伤,或爱和愉快的感觉,而是简单地看着她的脸,试图逃避她脸上“责备或受伤的表情”,或通过在她脸上制造“快乐的表情”来让责备或受伤的表情消失。换句话说:缺乏对他人的感受、想法、反应和行动的共情性理解,这些患者一方面“看着”,另一方面又对他们自己状态的具体的“可见”的表达“闭上了眼睛”。他们通常对别人不太明显的、间接的、微妙的情感表达很不敏感,这方面他们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愚钝。这种倾向——把他人和自身的精神表现当作具体的事物来对待——解释了否认外在现实和否认内在现实在人际关系领域的协作是非常容易的。
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些病人身上,不仅有一种普遍的精神贯注转移到知觉和统觉领域的现象,而且他们还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去知觉和统觉精神表现,就是将他们视作客体或自己的某些具体的部分。撤销对痛苦的感知和统觉的精神贯注,同时对理想化体验加强观察和过度精神贯注,从而从想象中移除不愉快的体验,并由愉快的体验取而代之。
更仔细地检查这种精神现实的具象化,我们意识到它必须充分利用隔离和断连(disconnection)的过程。一方面,它必须包括对精神单元(psychic units)的切割;但是,另一方面,被分割的部分通过合并和分类重组,往往会从具有抽象功能的变成新的类似具象化的复合体。事实上,我们观察到F先生不仅将幻想和想法与相关的感觉分离,甚至与相应的行动分离。然后,他分别且极端地处理这些不同的精神部分,仿佛是在处理自体中那些相互独立的、具体的、意象的部分一样。就算不考虑不同的参照框架,他也倾向于隔离,融合成很多单元(units),并从整体上否定所有发生过的那些精神元素(psychic elements),例如,那些太过接近意识且同时含有一种无法接受的精神内容。
这种运作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否认不像压抑那样以一种选择性的、有针对性的方式起作用,而是以一种大规模的、整体性的方式起作用,它很容易诱发一种不分皂白的、集体的防御过程,移置和移情的表现扩展到所有的客体、领域和活动。我们强调,F先生不是受困于有针对性的抑制,而是广泛性抑制,并且不会对特定的情感反应有所反应,表现为某种具有广泛性的心境状况;因此,他抱怨没有良心,没有激情,没有思想,没有性需求,没有攻击性,也没有快乐这些全部。列文对轻狂躁患者隐藏情感的描述说明了同样的观点。
我在引言中指出,否认的巨大影响可以在健忘症的特殊性质中很好的被观察到,特别是在那些大量使用这种防御的病人的遗忘中。这一点使否认与压抑之间的合作问题重新成为焦点。F先生参与了对这种遗忘的研究。他的婴儿健忘症覆盖了他的第一个童年时期,是如此完整,以至于好几年的分析材料都没有给出关于他三岁半时的创伤事件的任何线索。他竟忘记了这段不愉快的时光,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他的母亲曾经反复谈起这件事。病人要么是“没听”,要么是“听了但没问问题”,要么是“马上又忘了”。这也是他对当前冲突的典型态度。每当他体验到一种不良情绪活动起来,他就会简单地“不参加”,并设法迅速忘记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换句话说,他会同时将注意力从外部刺激和内心反应中抽离出来,然后立即不加选择地抹去围绕着这个特定的、令人不安的冲突的所有内部和外部体验的记忆,而不是去应对当前这个具体的冲突。在他的分析中,患者难以倾听和回忆令人不安的治疗小节,这无疑表明,在这种类型的健忘症中,压抑作为辅助防御与否认内部和外部现实密切合作。问题是,通常情况下,否认会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和协助我们所谓的对记忆的压抑。
我们回想一下我之前的评论,婴儿健忘症不仅涉及对本能驱动表征(instinctual drive representations)的防御,而是肯定会远远超出这一过程,延伸到感知觉的领域。联系弗洛伊德关于“恋物癖”的论文,我们已经进一步指出,源自于对现实的否定和扭曲的想法,可能会实实在在地和深深地受到压抑,例如被阉割或有阴茎的女人的概念。为了重新检验在婴儿记忆的遗忘中起作用的防御,我们可以参考一种典型的例子,比如儿童期的性体验往往是容易被遗忘(压抑)的。
一个处于生殖器期的小男孩不小心看到了正在厕所里小便的父亲的生殖器。这种经历的各种记忆成分以及它们可能的变迁会是什么? 他的记忆首先包含与事件感知相关的元素,如看到阴茎,父亲在小便,整个场景的相关设置,以及父亲在事件中的情绪表达和行为。但从防御的角度来看,记忆的重要部分是小男孩的内心体验,即他对这些刺激的各种情感和本能反应。在这一点上,我想参考我前面的观点,感知在本能的渴望和恐惧的影响下会立即被扭曲。正如孩子对被阉割或生殖器女性的理解所显示的那样,婴儿对客体和自体的想象总是混合了对外部现实的感知和在本能冲动和冲突的影响下产生的幻想。因此,男孩的各种本能反应,他的同性恋冲动和敌对冲动,不仅会在对特定场景的感知记忆中得到具体的表现,而且还会在父亲形象和他自己形象的持久印记中得到具体表现。只要它们是痛苦的,作为最早的原始防御形式,这些具体的和意象的元素就会被否定,这样就可以实现对记忆的遗忘。
但是,在发展的这个阶段,这种体验带来的对阉割的恐惧,肯定需要更激烈的措施。随后,一个真正的防御过程将开始,直接和具体地针对不可接受的本能冲动,即针对被禁止的性欲和渴望敌对的幻想,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种压抑的过程最终会把那些原本已经被否认排除的记忆元素都拉进潜意识中。
总而言之,我们难免猜测导致婴儿健忘症的防御过程通常会利用否认来准备和帮助消除意识中那些痛苦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既来自外部的事件也来自内部的想象,包括那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本能驱力和恐惧的具体表达。在防御过程中的一种病态的普遍否认不但反映在上面提到的婴儿健忘症的特性中,还体现在可获得的婴儿的记忆材料中,它暴露于不寻常的和激进地对外部和内部现实的扭曲,过去和现在,沿着非常明确的路线,这是压抑所无法企及的。
现在,我们把神经症性否认及其与压抑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放在一边。但在讨论我们的下一个主题,精神病性否认之前,我们必须指出否认和另外两种古老的防御机制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发现这两种机制是F先生防御操作的组成部分。如果精神表现重新恢复了客体和自体的某些部分或者具象化的形象,那它们理所当然需要把自己借给内射和投射这一原始过程。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否定的集体性的行为模式和压抑的更有选择性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区别,使人立即想起早期婴儿原始的认同形式与在更成熟阶段对自我和超我的更高级的认同之间的类似区别。与否认一样,第一种是基于将好的或坏的客体全部或部分地融入自体的具象化的想象中。在更高级的阶段产生的认同也涉及到内射和投射的机制;但就像压抑一样,它们代表了选择性的过程,因为这导致从爱的客体那里接收过来的某些标准、态度和性格特征的发展。
F先生的案例材料有助于研究否定与这种原始的内射和投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讨论了患者对自己坏的或可怕的部分的否认、否定(disowning)和投射到外部,并简要地提及了潜在的施虐受虐认同,这种认同源于将坏的、施虐的、受伤的、责备的和惩罚性的母亲揉合在一起的原始幻想。
我们知道,婴儿时期的对母亲的严重失望和被母亲遗弃的经历,就像这个病人一样,可能会导致一种古老的认同机制的倾向。像他这样的案例,或者像V.H.Rosen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报告的一个有趣的案例,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创伤性的暴露在令人恐惧的感知觉中,尤其是在前俄期,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一种大量使用否认的特殊倾向?在其他一些以否认为主要防御机制的案例中,我发现一些童年早期的创伤性、恐怖的事件会突然被感知到。有一次突然看到的是一个实施自杀的垂死母亲;另一次是一位被抢劫和谋杀的母亲;第三位是在孩子面前突然流产的母亲;在另一案例中,持续性的暴风雨般的原始场景体验一直持续到九岁。
在F先生的案例中,我确信母亲的流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她的疾病和抑郁,还有这些痛苦疾病和兄弟死亡所带来的体验的复活,都说明在他的防御操作中否定加上原始的内射和投射机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显然,我的病人在三岁半的时候,他的自我发展还不够成熟,无法成功地应对创伤性事件突然引发的巨大的情感冲突。
事实上,这三种原始防御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从能量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们显然都与大量去中立化(deneutralization)的驱力能量一起发挥作用。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否认机制背后所隐藏的原始的杀人幻想在他的谋杀想法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精神病以及精神病性防御和神经症性防御的问题上。正如我先前所言,我相信在精神病患者中本能的退行性去中立化(the regressive deneutralization)和融合化(defusion),以及大量攻击性力量的涌现,是造成自我和超我功能崩溃的原因,是高级防御模式被原始防御模式取代的原因,也使这些原始防御具有精神病性的特质和功能。
从这个角度比较压抑、反向形成和那些高级认同方式与否定、原始整合(primitive incorporation)和投射机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超我使用少量中立化攻击(neutralized aggression)对付自我,或自我同样如此对待本我,似乎可以使自我,在具有中立化特性的反精神贯注自我组成物的帮助下,抵御特定的、有选择的无法接受的驱力组件。与此相反,否认和古老的内射投射过程则使用大量的非中立化攻击(和敌对的性力量) 分别用于对抗危险的自体和客体形象或外部客体。
将这些想法应用于精神病,精神上的冲突导致对性和攻击性驱力极端的精神贯注从一个客体或客体形象(object-image)转移另一个,或从客体到自体,或反之亦然。我们确实观察到,精神病患者不仅改造功能性的精神单元,而且改造整个功能性系统,如(自我)本我或超我(自我),变成全能的客体或自体形象,只要它们是危险和可怕的,就会被攻击和根除。
我们熟悉躁狂和抑郁状态背后的机制。只要指出人格化的施虐的超我对坏自体的大规模攻击就足够了,这导致在抑郁期自我功能的普遍抑制,或在狂躁时期超我被完全推翻,使得自我与本我可以联合起来。
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会明确无误地表达他们对本我或超我的憎恨。例如,上面提到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孩,在某些时期会在所有层面上无情地扼杀所有本能努力,无论是攻击性的还是性的。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故意停止一切性活动,禁食,停止吸烟和饮酒,同时避免与女性或男性进行任何危险的、有诱惑性的接触。最后,他会通过割掉自己的阴茎来表达自己摆脱邪恶的愿望。很难确定在这种疯狂的、普遍的防御性努力中,压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参与其中,或者仅仅是古老的防御在起作用。无论如何,性和攻击性的驱力表现在这种时候会完全消失。想象一下这种全面防御所需要的巨大努力,我们对它一定会失败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个男孩身上,我可以观察到他过度紧张的自我是如何逐渐陷入困境的,一种空虚的状态,紧张型抑郁会发展成完全无法工作,伴随着死亡和迷失自体(loss of the self)的感觉。然后突然之间就会出现中断;病人会反抗,会表达他对所有禁令或对代表他们的权威机构的仇恨。从一天到另一天,本我将重新出现,并建立其绝对的权威。一种焦虑、偏执的精神病状态会伴随着病态的进食、不间断的自慰,以及不断变化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形态多样的倒错(polymorphous-perverse)幻想和我在引言中描述的那种杀人冲动。
我们认为,在精神病患者中,压抑和其他更正常的防御机制会失效,并被古老的防御过程所取代,但否认、内射和投射并非精神病患者所特有;在神经症中,我们发现这种原始的防御与压抑相互协作、相互作用。那么,精神病性和神经症性的否认、内射和投射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必须问,首先:我们将某些机制定义为精神病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M. Katan呼吁关注精神病患者人格中的非精神病性部分,他认为只有导致妄想症状的补偿机制(mechanisms of restitution)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性的。但是,如此严格地区分人格的精神病性和非精神病性(准精神病)部分,以及精神病性(可恢复性)机制和非精神病性(神经症性和准精神病性)防御,是一种过度简化,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误导性。
首先,在谈到精神病患者人格中的非精神病性部分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精神病患者的人格结构和防御系统与潜在的,甚至是在准精神病阶段之前的,精神病患者的人格结构和防御系统之间明显的本质区别。我指的是它们有缺陷的结构分化,它们的自我和超我功能的脆弱和不足,它们的压抑能力不足和古老防御机制的盛行,这些特征我已经在我的介绍中指出。我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个我在我的书(1967年)中讨论过的要点:潜在的或门诊的精神病患者倾向于将他们的冲突外部化,表现出来,并利用外部客体和现实来帮助他们失败的防御。通过对两名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两名潜伏期儿童的观察,我正确预测了他们未来的精神病崩溃,使我确信,这些容易诱发精神障碍的缺陷在潜伏期开始时就明显存在了。
的确,同样是这些机制——隔离、否认、内射、投射——当显性精神病发展时,他们容易被假定为精神病的特质和功能。他们此时不是被用于对本能的防御,他们将,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精神病性的“丧失和补偿(loss and restitution)”过程。与压抑相比,它们古老的特质更加适用于这个目的。因此,在显性精神病阶段,我们有时会同时发现“非精神病性”和“精神病性”的否认、内射和投射。
此外,值得怀疑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只把补偿机制视为真正的精神病性的。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当一个病人憎恨并试图杀死和根除所有的本能或超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病类型的防御。不仅是补偿机制,还有那些前面的客体丧失所导致的结果,都表明了某种防御性的努力,这在本质上是精神病性的。
无论如何,使他们具有精神病性质的自我防御的功能性转变似乎依赖于上述讨论的在精神病性过程中发生的驱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退行性变化。至于神经症性与精神病性的否认、内射与投射之间的区别的决定因素是精神病患者的退行程度。
再重复一遍:使用这种防御的神经症性自我已经部分退回到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内部的精神现实,尽管与外部现实有明显的区别,但仍然被以同样的具象化的方式对待。虽然神经症性的否认可能涉及精神元素(psychic elements)的断连、隔离和集体汇合(collective joining)的过程,这将它们变成类似具体的、图像的单位,并且保留他们精神上的本质。即使考虑到我在F先生身上观察到的,这些内射和投射,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之间的界限仍得以保存。
然而,在精神病患者中,病态过程导致精神表现的真实破碎、分裂、具体化和外化,赋予他们真正的具体化的性质。最终,我们在本质上是抽象的和精神的,与具体的和物质的之间,找到了一个等式。就像那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孩,他会把本能努力首先与邪恶划上等号,然后与坏的阴茎或坏的客体划上等号,从而希望通过切断生殖器或杀死坏人来摆脱本我。
我们熟悉精神病性的对抽象的具体化,哈特曼在他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论文中重新讨论了这一点。它涉及到连续的、古老的内射和投射过程,导致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之间的混淆;在客体和它们内心的形象之间的混淆;在对客体和客体刺激的感知和对它们的内在反应之间混淆;以及最终在客体和自体之间的混淆。其结果可能是分裂的元素或自体的部分与客体之间的妄想般的融合,即我在之前的论文中讨论过的精神病性认同。
关于精神病性具体化,哈特曼还重新讨论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精神病患者将词语与其意义分离开来,将精神贯注从抽象的思想转移到可具体感知的形式上的(formal)词语符号,将后者转化为客体的替代品。如果将弗洛伊德的论点加以扩展,我倾向于相信精神病患者可以转换的客体替代品不仅是语言,还包括任何可以分裂的、形式上的精神元素,例如情感表达的组成部分,如哭泣、大笑、手势甚至行动。我很感谢西尔伯曼博士(Dr. Silbermann)的观察,他的观察证实了这个想法。他问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孩为什么会笑,这个男孩经常发出不恰当的笑声,他得到的回答是:“那是约翰尼。”笑本身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客体,约翰尼。我们同样可以假设精神分裂症的特殊习惯可能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功能。
让我回来,从精神病性防御和精神现实的精神病性具体化的一般问题,回到我们专注的话题:否认。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否认和扭曲现实在精神病发展中的复杂作用;我更想集中讨论一个特殊的问题。对外部和内部现实的大规模否认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对自体和客体精神贯注的精神病性撤销?我们记起病人对他的良心和本能的否认和否定,导致内心的空虚和死亡的感觉,尽管从来没有到害怕失去自我(loss of the self)的地步;此外,他对母亲的冷漠源于他想要伤害她并且让她责备的目光消失。
否认与客体的和自体的精神贯注(object-and self-cathexis)的精神病性丧失(psychotic loss)之间的关系当然需要临床和理论的深入研究。但我们可以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倾向于通过感官而非情感链接将自己与客体联系起来,在相反的情况:他们可能通过逃避和避免性接触、触摸、气味、观看或聆听客体来与客体分开。那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孩会试图避开危险的男人或女人的视线,以此来显示自己从客体世界的撤退。当他遇到这样的人时,他会真的闭上眼睛和耳朵,并且把他们分裂出去,以达到对他们的精神撤离(decathect);而对于好人他则会通过观察、模仿和吸入对其进行精神贯注。
另一个病人拒绝见他的父母,因为与他们保持距离会让他觉得自己对他们就像对远亲一样。当他重新建立起与父母的关系时,他看到了他父亲的形象,这个在他内部“被锁起来和隐藏起来”的形象,他的身体“直到膝盖以下”的部分在视觉上重新显露出来;他非常害怕这张照片,于是他迅速地试图通过“再次锁上它”来让它消失。这位病人带着母亲的照片,一整天都专注地看着她的照片,从而恢复了他对母亲的感情。我们注意到,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感受的丧失和复活都是通过与客体的形象相同的外部图像的视觉上的消失和重现来完成的。
在总结这篇论文时,我想要回到我的出发点:在某些精神病患者中,本我的内容变得明显的轻松与婴儿健忘症的不受影响的特征之间的不一致。事实上,这些现象之间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它们是相当一致的。这些记忆和大量的记忆缺陷都建立在否认和扭曲现实的这一相同的广泛基础上,而它们目前的病态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健忘症不是真正驱力压抑的结果;这是本我入侵自我和难以揭开婴儿期历史面纱的原因。对过去分析性的恢复和重建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具有现实检验的,明确历史时期的,分组(grouping)且合适的驱力表征,并且这些驱力表征能够整合到一个有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历史现实背景中去,他越是否认或者与现实失联,精神病性部分能力就越弱。有时我们观察到,当精神病患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现实检验的能力和使用更正常的防御手段,他可能会发展出处理过去的能力。
我们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困难,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对“记忆”和对过去重建的抗拒。我在上面说过,一般来说,否认的病人会表现出见诸行动的倾向。反过来说:见诸行动似乎经常与否认倾向联系在一起。从治疗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为了便于恢复和重建过去,我们努力使病人放弃他们的见诸行动,就必须主要面对他们对现实的否认和扭曲。
REFERENCES
Deutsch, H. Zur Psychologie der manisch-depressiven Zustände, insbesondere der chronischen Hypomanie Internat. Ztsch. Psychoanal. 19 358-371,1933 Ž
Eissler, K. R. An unusual function of an amnesia The Psychoanal. Study Child10: 75-8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5 Ž
Fisher, C. Dreams and perception: the role of preconscious and primary modes of perception in dream formation American Psychoanal. Assn. 2:389-445 1954
Fisher, C. Dreams, images, and perception: a study of unconscious-preconscious relationships American Psychoanal. Assn. 4:5-48 1956 Ž
Freud, A.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6
Freud, 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hapter 71900 Standard Edition 5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 Ž
Freud, S. The unconscious 1915 Collected Papers 4 98-136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5
Freud, S. The Problem of Anxiety 1926 New York: W. W. Norton, 1936
Freud, S. Fetishism 1927 Collected Papers 5 198-204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0
Freud, S. 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defensive process 1938 Collected Papers 5 372-375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0 Ž
Freud, S.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1939 New York: W. W. Norton, 1949
Hartmann, H. Contribution to the metapsychology of schizophrenia The Psychoanal. Study Child8:177-19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3 Ž
Jacobson, E. Contribution to the metapsychology of cyclothymic depression In:Affective Disorders ed. P. Greenac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3 pp. 49-83 Ž
Jacobson, E. Contribution to the metapsychology of psychotic identifications American Psychoanal. Assn. 2:239-262 1954 Ž
Katan, M. Structural aspects of a case of schizophrenia The Psychoanal. Study Child5:175-21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0 Ž
Katan, M. The non-psychotic part of the personality in schizophrenia Int. J. Psychoanal.35:119-128 1954 Ž
Kris, E. On preconscious mental processes Psychoanal. Q.19:540-560 1950 Ž
Kris, E.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in psychoanalysis The Psychoanal. Study Child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6 Ž
Lewin, B. D. The Psychoanalysis of El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50 Linn, L. The role of perception in the mechanism of denial American Psychoanal. Assn. 1:690-705 1953 Ž
Mahler, M. S. and Elkisch, P. Some observations on disturbances of the ego in a case of infantile psychosis The Psychoanal. Study Child8:252-26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3 Ž
Nunberg, H. On the catatonic attack In:Practice and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3
Rosen, V. H.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traumatic childhood event in a case of derealization American Psychoanal. Assn. 3:211-221 1955 Ž
Silbermann, I.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aelder, R. The structure of paranoid ideas: a critical survey of various theories Int. J. Psychoanal.32:167-177 1951
翻译|王媛 武汉忠德心理医院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