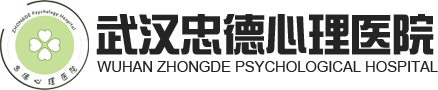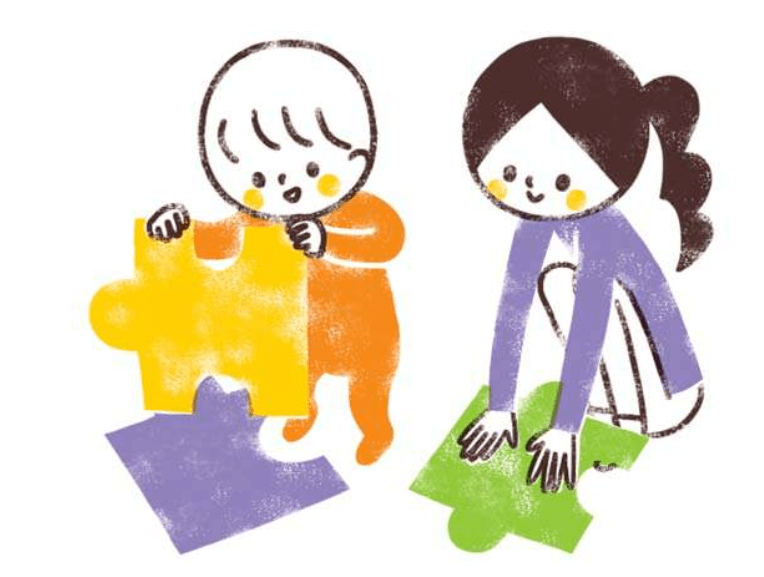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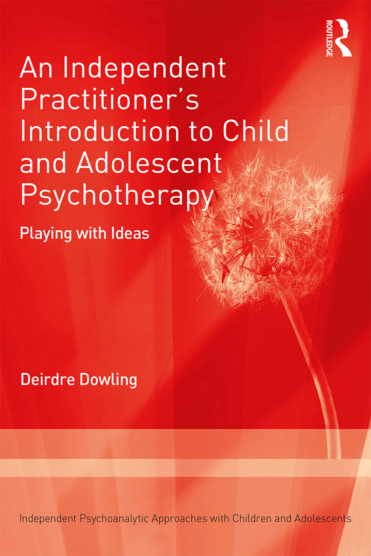



潜伏期儿童向心理治疗师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双重挑战:克服看似不动的甚至是迟钝的阻力,并解开和理解丰富而富有想象力的幻想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模棱两可。
(威尔逊 1989:59)

(兰亚多与霍恩1999:168)
安妮·阿尔瓦雷斯(Anne Alvarez)在她的《现场公司》(Live Company)一书中也讨论了对防御的类似尊重。她认为,对脆弱的孩子来说,建立一种防御结构可能是一种成就,可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不被痛苦的感觉所压倒。她建议我们,我们必须支持这些辩护,以免破坏他们管理自己和关系的努力。当我们思考无所不能时,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想法。无所不能是指孩子对权力或控制的一种防御,以此来对抗一种无力感。一个小男孩吹嘘自己很强壮,能在操场上和任何人打架。与其让他对自己太小而不能这样做的痛苦现实失望,不如让他更温柔、更支持到他自我的回应是,他期待有一天,他有力量与那些想要与他对抗的男孩较量。
Winnicott认为,当一个年轻人感到更有安全感,处于更有爱和更稳定的关系中时,这些潜在的需求感就会出现。照顾有身体或精神疾病的父母的年轻人,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虚假的自我,一种称职的角色,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这种角色可能会隐藏他们对养育的需求。在心理治疗中,一旦一个年轻人感到有一个可靠的治疗关系,就有机会分享这些更脆弱的感觉和未满足的需求,真正的自我意识开始显现。

一个儿童的防御模式,情感层面的功能,以及孩子与治疗师的关系质量,这些都是在考虑诠释时需要思考的因素。
安妮·阿尔瓦雷斯(Anne Alvarez)在她最近出版的《思考的心》(The Thinking Heart, 2012年出版)一书中,讨论了适合儿童情感发展和心理状态的三个层次的解读。她强调了我们说话的语气和用词的重要性,和所说的内容一样重要。
在第一个层次的解释中,儿童心理治疗师描述为什么某事会发生,并说明含义。“你不高兴是因为你迟到了,你觉得那是我的错。”对于那些处于更麻烦、更受迫害的心理状态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太复杂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治疗师认识和理解他们的经历的特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太沮丧了”。这是解释的第二个层次,重点是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她指出,如果孩子感到太过不安,那么以这种方式定位孩子的经历可能会感觉像是一种指责,或者可能会让孩子充满太多的情感。因此把它变成一个更笼统的评论会有帮助,比如“迟到真让人心烦”。
最后,她认为,对于那些非常孤僻、被剥夺的或心不在焉的孩子来说,他们不希望从治疗师或生活本身中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他们需要第三层次的解释。然后,她建议,重要的是治疗师要给出更积极、更强烈的回应,有时要提高声音。这样做的目的是赋予孩子前所未有的意义,让孩子重获新生。一个退缩的孩子可能会在治疗过程中享受片刻的玩耍,并且看到治疗师真的很感兴趣和有趣,可能会瞬间充满快乐和兴奋的感觉。正是这种体验需要治疗师放大和加强,作为参与生活的重要时刻。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玛丽身上,她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我做她的治疗好几年了。
在一节相当沉闷的治疗中,玛丽相当不感兴趣,心事重重,我除了建议我们用橡皮泥为她画一幅画像以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开始帮助她去做一个简单的衣服和头发颜色与她匹配的形象。当她看到它完成时,她既兴奋又高兴。
我也用愉快的语气说:“你真的很喜欢我们一起做模型,它看起来很像你!”
每周她根据她对自己的感觉来塑造一个,这让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模型。这是我们之间的一次重要的她可以主导的“对话”,这与她在早期治疗中表现出的被动脱离非常不同。
安妮·阿尔瓦雷斯称这种疗法为“矫正”,感觉孩子的部分自我正在被一点点地改造。她还表示,这个治疗过程是“朝着目标前进”,而不是修通。她强调,在“修通”成为可能之前,治疗师需要与更孤僻和不安的患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正如本章最后一部分所述。
治疗的过程是两种心理的相互作用,即患者的移情和治疗师的反移情。[这个]过程需要持续的自我监控能力,并在治疗过程中寻找观察这种互动的空间。
(霍恩2006:28)
观察一个人的感受和以理解年轻人心理状态的方式回应,是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的关键技能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技能会变得越来越完善。这种技巧可以让治疗师感受到年轻患者在治疗中所带来的关系的质量,并看到随着治疗工作的进展它是如何微妙地变化的。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将早年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模式内在化,这塑造了我们对他人尤其是那些扮演父母角色的人的期望,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这些早期和当前的关系被转移到治疗关系中,这些重要的家庭关系所唤起的情感、焦虑和希望可以被心理治疗师识别和理解。这就是移情关系。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对移情关系的情感反应被称为反移情,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我从年轻人对我的反应中提取语言和非语言线索。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玛丽的情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自闭症少年。她很少说话,但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她的孤独和困惑,她侧着身子走进房间,用手护着脸,偷偷地看着我。我能感觉到自己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回应她,不知道如何去接近她,感觉自己无法理解。在与这位年轻女性工作多年后,我想,在反移情中,我认识到她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中感到自己有心无力。她想和人们在一起,但很快她就在他们面前感到不知所措,这也是一种可怕的经历。
2016年的纪录片《生命》(Life, Animated)对这段经历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令我深受感动。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年轻的欧文·苏斯金德(Owen Suskind)向观众讲述了自己患有自闭症的成长经历。欧文说他多么想和人们在一起,但他不知道如何与他们接触。他描述了他和他的家人是如何努力沟通的,直到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他用迪士尼角色米老鼠(Mickey Mouse)的话语告诉他父母关于自己的事情。迪斯尼卡通人物说话的简单性和他们的活力,让欧文能够以一种比普通的家庭和朋友关系更轻松的方式接触到他们,他可以使用卡通人物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与自闭症儿童和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起工作教会我们在反移情过程中要密切接触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语言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感受。我们必须依靠非语言线索,以及我们在孩子面前的感觉来理解它们。有时候,我对病人的反应可能更多的是身体上的,而不是情绪上的。可能关于胃的紧张的本能反应,是由于我正收取着病人的焦虑,口腔干燥对我来说更像是恐惧,或者厌烦或嗜睡反应来源于一个心不在焉的孩子正关闭我的思考能力。当我的病人与我交流早期的前语言感受时,这些身体反应最常见。我可能会简单地试着把这些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太受迫害而听不进去了。如果我感到焦虑,我可能会说“这一定很令人担忧”,或者如果我感到自己被我的孩子病人拒之门外,我会说“这些事情可能很难思考”。
治疗关系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在这里移情感觉可以被探索和思考,新的联系方式可以被发现。随着这种探索的发生,一节一节治疗的慢慢进行,年轻人可以在这种新的关系中发现一种不同的联系方式,一种看待自我和他人的新方式,然后可以在其他环境中,如家庭和学校中试用。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个紧张而顺从的小男孩害怕激怒他的父母,他可能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治疗中感到沮丧,并允许自己向他的治疗师表达一些烦恼。他发现治疗师善于接受,甚至对探索这些感觉很感兴趣,这让他有信心尝试在父母或朋友面前表现得自信,去发现自己的新一面是否也能在父母或朋友面前安全地表达出来。这种外部变化可能只有在对年轻人的情感、焦虑和冲突进行大量探索之后才会出现,但有时这是父母看到孩子正在进步的第一个迹象。重要的是,父母也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治疗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欢迎这种新的自信的迹象。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一些治疗支持作为父母的自己,正如我在下一章讨论的,这将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些变化,也使他们能够度过当年轻人的行为可能变得更困难时的困难时期,如果负面情绪能在治疗中得到修通。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在移情过程中暴露于负面情绪是痛苦的,尽管我们知道这些负面情绪是来自患者内心世界的投射。他们感觉足够真实。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临年轻患者的诋毁、烦恼和拒绝,也可能会在患者康复后产生更加积极的感受。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必须找到一种平衡,允许自己被这些感觉所触动,认识到它们,但不要被它们以一种无益的方式所控制。除了移情关系之外,我还努力与这个年轻人保持一种治疗联盟,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之间的信任基础上的。这让我重新与治疗任务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强大的移情感觉可能会使治疗过程变得艰难。在这个过程中,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管理治疗结束非常重要。一起整理一间凌乱的房间,或者帮助一个年轻的少女做好准备重新面对这个世界,都有助于年轻人在面对这个无法抵抗的主观现实时,为其重新树立一个普通的世界。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对病人的情绪反应,会随着治疗的进行而改变,从而引导我们意识到我们之间关系的质量会随着治疗的进展而改变。我将在下一个关于变化过程的小节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在心理治疗中,我们把带来恢复的缓慢治疗过程称为“修通”。这个短语体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问题序列的经验,当他们在治疗中出现时,遵循病人的无意识心理的逻辑。这是一个与由治疗师以更直接的方式引导的更多聚焦于认知解决方案的疗法不同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把这些原因放在一边,不考虑转诊,也不考虑年轻人的行为和情绪困扰。事实上,孩子们在治疗和外部世界里不断地用他们的不良行为和不良情绪以及定期与父母回顾他们的经历都在提醒我们这些问题存在。但我发现,我只能通过让病人自由地思考来决定治疗的内容,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议程来发现孩子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常常有不平衡的进展。当情绪问题出现时,可能会导致早期行为困难的倒退,然后当面临挑战时,可能会出现飞跃,年轻人获得新的信心或自我理解。
将“修通”分为三个阶段可能会有所帮助:治疗的早期、中期和最后阶段,无论治疗持续三个月还是两年。
心理治疗的早期治疗阶段有时会让人感到困惑。我经常发现很难理解治疗材料和我对孩子的情绪反应,我想知道这一切的发展方向。怀疑和不确定的治疗过程是很重要的,随着迷雾逐渐消散,某些主题将成为治疗开始阶段的中心。我用一系列孩子每周在沙盘里玩耍的照片来说明这个逐渐清晰的过程。她让我把这些作为她作品的记录。
珍妮八岁了。她是一个有点害羞的女孩,如果她感到受到威胁,就容易爆发愤怒,而且她经常会退缩到沉默。她好几个星期都不跟我说话,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唯一直接的交流就是玩沙盘。几个月后,我们把照片按顺序摆放在桌子上,我着迷地看到这些照片是如何反映她的治疗进展的,这是我直到那时才意识到的。第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一群乱成一团的动物和人,她把它们放在沙滩上,这些静态的场景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接下来的一系列图片更简单明了,呈现了一个灾难场景和一群无法移动的人物。有一家人,一个女孩和她的父母带着几只动物,他们被撞坏的汽车和飞机包围着,机头一头扎进了沙子里。还有一个精灵,滑板上的米老鼠,和两个摔跤手,但是,她告诉我,这些是冻结不动的人物。
我仍然不确定如何将这出戏与珍妮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我认为她在向我展示她的精力和想象世界是如何冻结的,因为她害怕一场情感灾难,或者她过去经历过一场灾难。我没有试图去解释,和她自己的生活有任何联系,因为我担心她会再次关闭。经过六个月的治疗后,珍妮变得更加开放、具有表现力,她的学校、她的友谊和她的家庭被虚构的角色赋予了生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与她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我可以帮助她更直接地思考她每周面临的一些情绪困扰,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
这幅作品展示了治疗过程的典型发展。几周后,反映了孩子内心生活的紧张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的主题成为治疗的焦点。随着治疗关系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分享和寻求帮助的地方,这些紧张关系开始被探索。随着治疗内容的演变,治疗关系的发展是变化的关键因素和晴雨表。珍妮一开始在感情上疏远我,我试图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她是担心我可能会批评她或打扰她,还是担心如果她让自己的嫉妒或愤怒情绪显露出来,她会勃然大怒?慢慢地,过了几个星期,她放松了下来,因为她觉得和我在一起更安全了,她确认了我会跟着她的节奏玩耍。最终,我们成为了盟友,一起探寻她内心深处脆弱的自信缺失,以及她受到迫害和不信任的感觉。
在我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与年轻人发展一种共同的语言,符合孩子的世界观和家庭文化。有时,谈话中出现特殊的词语或图像,成为治疗的隐喻,也许相当幽默。古怪的,或者像个外星人,是一些年轻人向我描述自己的方式。当我们探究他们对自己的感觉,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时,摆弄这些词及其不同的含义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工作的进展,这些最初感觉的自我厌恶或自我批评会软化成更幽默的自我讽刺,尽管有时这些自我认知很难改变,正如我在后面关于青少年的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
当病人和治疗师正在构建一个年轻人的问题世界的图景时,就把我带到了治疗的中间阶段。我希望现在就能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的兴趣,并取得了与我的病人治疗联盟(和充满希望的父母),这将帮助我们度过治疗的暴风骤雨阶段,那时这个年轻人会考验我处理愤怒和绝望的能力,并理解这些情绪的意义。随着年轻人僵硬的防御模式的放松,自我表达变得更容易,这让孩子自由地发展情感。随着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主题在几周内浮出水面,并不断加深。也许治疗过程的最佳形象是一个反复旋转的螺旋,每当螺旋旋转时,问题都会被重新审视,并从新的角度看待。一个认识、反思和理解的过程。
我知道,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特别关注的是找出事情出错的原因,我觉得这种知识将有助于儿童或青少年获得洞察力。然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们提出了一个对我们有意义的假设,但对年轻的患者却没有意义。然而,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当下,他们现在对友谊和幸福的渴望。与过去联系似乎无关紧要。
对其他人来说,回顾过去,看看问题是如何在父母的童年或祖父母的生活中开始的,可能会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心理治疗的后期阶段。看到这些模式可以防止年轻人觉得自己对家庭生活中的这些困难阶段负有责任。这些现在可以被理解为家庭故事的一部分。正如John byung - hall在他有趣的论文中所说,“家庭脚本:一个可以连接儿童心理治疗和家庭心理治疗思维的概念”:“让孩子认识到父母当前的行为是试图纠正他们自己的伤害经历,从而为宽恕铺平道路”(byung - hall 1986)。
治疗的最后阶段通常是有益的,甚至有时是令人愉快的。年轻人变得更加自信和自我意识,因为他们内化了一个更积极的自我意识,以回应治疗工作。他们找到了理解和管理自己困难感觉的新方法,他们可以回顾自己所做的治疗工作,并认识到自己取得的进步。在这个阶段,心理治疗自然地将治疗过程转移到帮助年轻人完成结束过程,承认他们的发展和发现,以及一些失落感,自由感和在治疗结束后更加独立的感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治疗方法都以这种直接的方式取得了积极的结果,我们将在书的后面思考破坏治疗工作的干扰和困难。
References
Alvarez, A. (1992) Live Company. London: Routledge.
Alvarez, A. (2012) The Thinking Heart. Hove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ion, W.R. (1962a) A theory of thinking. In E. Bott Spillius (ed) Melanie Klein Today: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1: Mainly Theory, pp. 178–186. London: Routledge, 1988.
Bion, W.R. (1962b)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Heinemann.
Byng-Hall, J. (1986) Family scripts: A concept which can bridge child psychotherapy and family therapy think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therapy 12(1): 3–13.
Freud, A. (1966 [1936]) The Ego and Mechanisms of Defence. London: Karnac.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J. Strachey et al. (ed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s 4–5.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
Horne, A. (2006) The Independent position in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M. Lanyado & A. Horne (eds) A Question of Technique,pp. 15–28. London: Routledge.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7: 99–110.
Lanyado, M. & Horne, A. (1999) The therapeutic setting and process. In M. Lanyado & A. Horne (eds) The Handbook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therapy, pp. 157–174. London: Routledge.
Life, Animated (2016) US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R.R. Williams. Brooklyn, NY:Motto Pictures.
Wilson, P. (1989) Latency and certaint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therapy 15: 59–69.
Winnicott, D.W. (1945) 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D.W. Winnicott (ed)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Collected Papers, pp. 145–156. London:Tavistock, 1958.
Winnicott, D.W. (1953)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4: 89–97.
Winnicott, D.W. (1960) Ego distortion in terms of true and false self. In D.
W. Winnicott (ed)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pp. 140–152. London: Karnac, 1965.
Winnicott, D.W. (1968)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fant and mother and mother and infant,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In L. Caldwell & H. Taylor Robinson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W. Winnicott, vol. 8, pp. 227–238.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