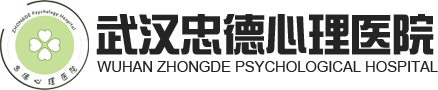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构成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弗洛伊德在探索精神分析理论的过程中,从最初的力比多、生本能本能开始建构,到他晚年,在结合了对战争的反思和临床工作的研究后,他提出生本能、死本能二元本能论。简单说,生的本能(或性本能)是建设性的,目的是生命和繁殖,是推动个体朝向外部世界发展能力和关系的;死亡本能是破坏性的,试图让个体回到一种既是死亡的,解构的,也是非存在的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通常很难观察到死亡本能的纯粹状态,因为人的出生时,生死本能皆有,只有在一些极端的状态下,比如自杀行为,可能才会观察到死本能达到极端值的一种表现。但是比较能观察到的死亡本能的表现通常是和攻击性,破坏性有关。研究生死本能的精神分析家认为,生、死本能的融合和去融合都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情况,比较理想的状况是一个人的生死本能是相互平衡的(这种平衡不等于数量上的均等,还是需要生本能要比死本能更占上风一些)且能充分表达个人的情绪感受,实现自己的关系发展,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一些病理性的情况会出现在两种本能过于离散或者两种本能以某种病态的方式给个体带来了一种精神生活和现实状态的损害。电影《周处除三害》是一个犯罪片,但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电影来理解生、死本能在个体身上的不同状态。


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陈桂林杀掉了香港仔,但在牛头/尊者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戏剧性的桥段。尊者用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首先让陈桂林的目标自动终止,因为牛头“已死”,而陈桂林的“脆弱”现状又正中尊者下怀,毕竟对于一个还残留了一些生本能的癌症患者而言,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都是对病者饱受折磨的一种莫大安抚,更何况这种希望会以一种魔法般的效果被亲自体验。这一丝生的渴望在陈桂林和张医生交谈病情的那一段也有体现,陈桂林走时留下一句话,让张医生去帮他找合适的肺去换肺。所以当尊者操纵使用了神秘、奇迹的方式来让陈桂林感受生的希望时,他一定会抓住并且相信。而当谎言拆穿时,尊者不过是一个邪教洗脑头领,当陈桂林要来戳破一切时,两方的对抗在礼堂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既是一场生与死的性命较量,也是一次基本人伦与人性扭曲的对量,一次个人意志与团体命运的碰撞。
在电影的进行中,无论是和警察的交手,还是击杀香港仔,处决尊者,在导演的安排下,我们几乎不太看得到受伤的陈桂林脆弱退缩,仿佛他浑身都被生的力量所加持,而随着目标的完成,他主动选择了放下屠刀,从心理和身体上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所以最后他临死前的表情,他是接纳的,微笑的。对他而言,人生的最后时期已经圆满。甚至,他展现了对超出于奶奶之外的人的一种感恩、感动,对社会的歉疚。

哲学家韩炳哲在谈到个体将自己豢养在徒劳的生命力里的现象时说到“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死之自由,那么他也不敢去冒生命之险,不能只身前行奔赴死亡的方向,而是在死亡中依赖自我,等待死亡。”他也引用了黑格尔所谈及的绝对精神的生命,不是徒劳的生命,“它不畏死,不怕生命之凋零,它承载并包容着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生命力源于‘死亡的能力’,它并非只重视积极面,忽视消极面。相反,它更愿意直面消极的部分,并与消极面共存,它的绝对性恰好体现在它直面各种极端和负面情况,并将它们包容在内——更准确地说,将它们封存在内。纯粹积极的、由肯定性主导的地方,是不存在精神的。”在陈桂林身上,“肺癌晚期”,举目无亲,违法犯罪都是他的消极面,是他无可逃脱的宿命,关心奶奶,解救小美,主动投案,感恩张医生是他的积极面,正是在这两方面的相互彰显之下,观众眼中的陈桂林这个人物形象变得立体丰满。
尊者的心魔世界
和陈桂林赤裸裸的杀人愿望不同,尊者的灵修中心是一个看起来一派祥和而背地里充满洗脑,控制,吞噬的地方。尊主给自己打造的人设是一个看起来充满源源不断的“生本能”的形象,他“仁慈”、“平和”、“赋于启发”、“疗愈大众”,当然维持这样的形象就必然有一群黑手套在背后支持他。所谓的平静祥和不过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催眠场,而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忍,随着小胖的中毒而慢慢解开,帷幕之下的尊者是一个将杀人与自然灾害相提并论的恶魔,而在他洗脑掌控之下的团体对处于无助中的小胖妈妈施加了恶毒的谋杀建议。

尊者不像香港仔,如果说香港仔在电影里展现的是较为直接的暴力、占有、掠夺,是一种破坏性本能远超于生本能的直接表达,那么尊者的内心世界更为扭曲,更处于一个精神病性的心理结构上,因为他的内心世界里,死本能(对外表现为清洗异己,建立洗脑团体,给信众投毒等)已经彻底劫持了生本能,并让原本应该服务于真实、深度人际关系,承认生命有限性的生本能转而服务于个人自恋,服务于巩固个人在团体里的绝对权威。尊者构通过非常分裂的方式建了一个被过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世界,在这里,代表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个体身份被舍弃,哪怕是和爱的客体相连的部分(如陈桂林的手表,小胖妈妈的结婚戒指)也被描述为阻碍,个体性的特征会被抹除(都穿着白衣服,剪除头发,唱洗脑歌……),而与之对应的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神迹般的人。这个人看起来打造了一个超脱、无痛苦和自由的世界,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对真实世界和关系的反对之上。

精神分析家罗森菲尔德曾经在描述这类精神病性的自恋病人时,说到:“这个妄想世界中的破坏性冲动有时会公开表现为过度残忍,用死亡来威胁自身的其他部分,以宣示自己的力量,但更多时候它们会伪装为全能的仁慈或拯救生命,承诺为病人提供快速、理想的解决方案,解决他的所有问题。这些虚假的承诺意图使病人的正常自我依赖或沉迷于他的全能自我,并引诱正常的理智部分进入这个妄想的结构、以便禁锢他们。”“事实上,如果病人的依赖部分,也就是他人格中最理智的部分,被劝说远离外部世界,并将自己完全交给精神病性妄想结构去支配,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精神病状态。”电影描绘尊者劝说小胖妈妈杀死陈桂林的桥段,是他内在的死本能试图进一步挟持他人生本能的过程,他指出别人心中的心魔,殊不知他就是最大的魔。信众的盲目跟从展现了那些被精神控制处于某种“急性精神病状态”下失去现实检验力的样子。
对比之下香港仔对小美还只是身体控制,小美在精神上很明确的保留了自己精神上的不服从,而在尊者这里,他建立的是一个由强大的死本能统治的恐怖中心,这股力量会绞杀每一个试图靠依赖,靠奇迹摆脱痛苦之人心中那本已薄弱的理智,夺取他们的心智,并将那些残余的心灵打造为一个清理“叛变者”,一致枪口对外的团体,以防止建立于虚假之上的伪善坍塌。

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并不是只有积极的生命面,因为消极对于保持生命力的状态也是必要的,一件事物,一个人体现出矛盾性且具备容纳和接受这种矛盾性的能力的时候,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状态。在电影里,尊者致力于打造虚幻极乐,否定生之痛苦,否定生死相依,陈桂林展现的是试图跳脱限制但被矛盾性牵制最后臣服回归的路径。尊者倒在“新造的人”的谎言之下,陈桂林的死是回归社会性,回归他自己,如果还有下一世,也许他会想做一个新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