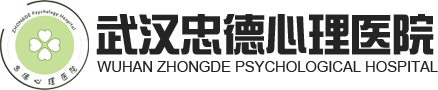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1985)精神分析回顾,72(3):379-402

“具体的”是一个形容词,用来形容多种临床现象,而这些现象之间乍一看没有任何关联。我们习惯于用具体来描述病人的一种思维混乱,漫无目的的状态,使得病人无法在自己的联想之外去认识它。临床医生也会把具体用在从躯体受损的人那里寻找具体的线索,以解开已被忘却的记忆。具体也可以描述抑郁症患者看似不可逾越的苦难,尽管分析师竭力告诉他们自己的理解,但病人们仍然不可避免地沉湎于不快乐之中。贯穿这些事例的共同主线是具体的病人被禁锢在当前的处境中(来自一个侵入性想法的压力、试图找回一个丢失的想法的绝望、以及看似无休止的抑郁症的迷雾等),这给所有的经历投下了一个意义狭隘的阴影。具体化的病人无法将自己从当下的紧迫性中解脱出来,并被困在一种无法超越自身的思维状态中。我将用 "具体 "一词来概括这种跨越多种临床表现的总体功能模式。
矛盾的是,尽管广泛使用具体性来描述临床现象,但文献中却很少关注对支撑它的心理过程的理解。一些明显的例外来自于发展心理学家的工作,如皮亚杰(1945,1954)和维尔纳(1957);然而,这些研究只专注于认知发展,他们的发现与任何人际关系的成长理论没有联系。即使在精神分析界内部,也只有少数作者讨论了具体性的临床表现、客体关系以及两者背后的心理过程之间的联系(比昂1957,1959,1962;布朗1980,1984;克莱因1930;希尔莱斯1962;西格尔1957,1878)。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具体性的亚类型进行区分。在这种分类之后,我们将用一种发展的方法来追踪具体性在认知和人际领域的路径和命运。这一观点将系统地把认知的成熟与客体关系发展的具体方面联系起来,并将对具体性的理解用于研究心理表征的形成。最后,讨论将集中在治疗的含义上。

在文献中,具体化被用来描述几个不同的心理过程,为了讨论的目的,这里将单独考虑。然而,实际上,这些亚类型紧密相连,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回顾文献时,我建议对具体性进行四种分类,它的用法围绕着这些分类。(1)器质性的具体性(Organic concreteness);(2) 地形的具体性(Topographic concreteness);(3)符号学的具体性(Semiotic concreteness);以及(4)互动的具体性(Interactional concreteness)。
我将器质性的具体性作为一个独特的亚型,是因为它具有普遍的不可逆转性(某些创伤除外),而且它出现的原因伴随着可证实或推断的病变、肿瘤、感染等。戈尔茨坦(1939年)对脑损伤病人的经典研究使他提出了 "具体态度",这些人的特点是,他们受制于直接经验。特别是短期记忆的明显中断,伴随着空间、运动和其他感知的扭曲,以及抽象思维能力的几乎完全丧失,使其与其他具体化的亚型区分开来,在这些亚型中,抽象能力可能被暂时抑制,或者可能随着具体的认知形式而发生波动。这个亚型也包括因智力潜能低下而导致的具体化。
该类型与其他形式的具体性在症状上有相似之处;然而,如果想要减少具体性,那是无法通过心理治疗来实现的。由于器质具体性的起源是在躯体领域,因此进一步的讨论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
在《梦的解析》第七章中,弗洛伊德(1900年)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幻觉性的梦境意象,他称之为 "地形回归法"。在追踪睡眠期间寻求表达的冲动的路径时,他观察到运动放电(语言或非语言的)在睡眠时被阻断。为了允许部分满足,发生了从运动到感觉和知觉系统的心理回归。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实际的感知事件(幻觉)代替了在清醒时通过行动获得欲望的对象。因此,在地形回归的概念中,弗洛伊德勾画了一条心理路径,从一个感知事件开始,发展成一种感觉体验,然后可能在运动方面得到释放。这样人们就有了延迟行动的能力,就会产生更抽象的思考能力。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感知事件→感觉事件→行动→ 思考。
地形上的具体性指的是用较低的事件体验模式代替较高的体验模式。由于只有抽象思维与"看"到眼前情况之外的能力有关,其后的所有内容如行动、感觉或知觉模式都是趋向具体化的。有几种形式是这种情况的代表。见诸行动是地形性具体性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行动代替了语言表达。只要行动持续存在,重复的行为模式就会继续下去,而个人无法从其直接经历的事件中提取任何意义。转换反应和许多心身症状都是地形性具体化的例子,它是由感觉事件取代行动或思维模式而产生的,从而使病人陷于一种体验之中,与当时的感觉之外的任何意义相去甚远。此外,地形上的具体性也可能涉及情感(通常是一个主要的感觉事件)作为感知的表达,特别是作为视觉幻觉,这是一种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所能观察到的具体性(Arieti, 1974; Searles, 1967; Storch, 1924)。

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研究符号和它所象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个词可能代表一个物体的方式。符号学的具体性一词描述了一种功能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抽象的思想被其最初所指代的感知内容所取代,导致符号物(或称能指,译者注)和符号意义(或称所指,译者注)之间的混淆。因此,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无法想到一棵树,但可能在实际的视觉图像中体验到一棵树。在其他情况下,符号学具体化的病人可能会把这个词体验为等同于它所指的对象。符号学具体化发生的过程与支撑地形学具体化的回归直接相关;然而,符号学具体化被列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因为它对客体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在下一节讨论)。弗洛伊德(1900)认为,每个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它的知觉根源,并区分了作为初级过程特征的 "知觉认同 "和次级过程的 "思维认同"。在初级过程中,词和它的知觉身份是等同的(在符号学上是具体的),而次级过程则意味着词和它的知觉身份之间是有距离或分离的(弗洛伊德,1915a,1923)。
符号学的具体性也被其他作者用各种术语描述过。Fenichel(1945)的 "前意识的幻想思维",Federn(1952)的 "思想向现实的回归",Fleiss(1959)的 "具体化",以及Arieti(1976)的 "感知化 "都提到了这里所说的符号学具体性。Fenichel(1945)强调了 "客体和客体的概念"(P 47)之间缺乏区别,这预示着Rosenfeld(1955)和Searles(1962)的报告将符号学的具体性与自我和非自我模糊的人际模式联系起来。因此,符号学的具体性被假设为人际关系模式的一部分,在这种模式中,自我和客体之间的通常界限要么模糊,要么不存在,要么被抹去。
互动的具体性发生在心理治疗的病人身上,尽管他们用语言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但是听上去他们似乎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说,而且可能显得沉闷、密集或难以琢磨。虽然他们可能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甚至超常的智力,但这些人却声称自己头脑迟钝、粗枝大叶,无法理解临床医生的干预措施。互动具体化的病人没有表现出器质性、思想混乱的外在迹象,他们的字面意思不能用器质性、地形学或符号学的具体化来解释。这些病人在许多临床报告中都有描述,尤其是Giovacchini(1972)和Langs(1978a,1978b)的描述特别清晰,他们都强调这种类型的具体性的适应性目的是保护病人不出现痛苦的情感。Giovacchini(1979)还强调,一些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具体化地坚持他们的无望感,以此来防止人格进一步崩溃。
互动的具体性也可以在阻抗治疗的背景下看待。Racker (1968)讨论了病人与分析师解释的关系的性质,并观察到,根据病人冲突的性质,干预可能被体验为生殖器的侵入,或者,可能是温暖、舒缓的牛奶。在这方面,互动的具体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阻力,源于无法 "接受(Take in) "解释,因为它们对病人有无意识的意义。最后,正如Langs (1978a, 1978b, 1982)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明确描述的那样,这里所描述的互动性具体化可能是由不良的治疗技术发展而来。由于训练不足和反移情困难的结合,临床医生可能会刺激并强化一种 "治疗阴谋",其特点是在治疗中陈旧,没有心理意义,而且可能充满了空洞的陈词滥调。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提供一个发展模式,把具体性、整体认知发展、客体关系的增长和心理表征的形成等组成部分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来自马勒、克莱因、皮亚杰、温尼科特以及英国精神分析学派的其他人的观察将与作者以前的一些工作结合起来,以产生一个关于生命头三年中具体性蜕变的多面性观点。
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处于自闭症阶段的婴儿(Mahler,1968,1975)主要是被努力实现生理稳态的反射所支配。克莱因派(Bick,1968;Grotstein,1977a,1977b;Meltzer,1975)把这个阶段称为粘附性认同(adhesive identification)。婴儿被视为试图尽可能多地将其皮肤表面的区域附着在母亲身上,以便将皮肤表面作为身体自我的外部界限。正如我在其他作品中提出的(Brown, 1984, 1985),正是从这种包含一个封闭的内部空间的经验中,发展出一个在其中可以进行思考的"心灵"。Deri(1972)从温尼科特关于内部空间理论的参考框架出发,也强调了这些早期的结合经验对于创造一个内部空间的重要性,这个内部空间是 "心智 "发展的中转区,客体被投射到其中。这一时期的失败可能会导致Grotstein(1979)所说的皮肤边界缺陷,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个人的思想对他人的看法是开放的,以及一种无法坚持思想或冲动的感觉。
比昂(1962年)区分了思考的心灵和被思考的心灵内容。在这方面,他说,在早期发展中,或在严重的精神病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没有思考者的思想。就自闭症/粘附性认同阶段而言,由于正在逐步界定心智所在的空间,所以说任何与认知有关的过程都在发生,这是不正确的。然而,我们也许可以安全地得出结论:虽然没有心智来 "思考 "这些内容,但还是有心智内容的存在。我们必须假设这些原始思想是以模糊的神经生理事件的形式出现的(Jacobson, 1964),这些事件可能通过幻觉被重新体验("思考")(Ferenczi, 1913)。在弗洛伊德的地形回归模型中,婴儿被具体地与当下的感知数据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可能类似于急性精神病患者失去理智并被大量的精神内容所迷惑。
皮亚杰(1952年,1954年)和马勒一样,关注出生后第一个月主要行为的感觉运动反射,但没有解决假设的心理内容问题。克莱因(1952年,1957年)在发展她关于幻觉的想法时,在皮亚杰和马勒对反射和假设的心理内容的完全关注之间提供了一个桥梁。在她对本能的研究中,假定认知成分与弗洛伊德(1915b)所讨论的本能的其他方面(如来源和目的)相关联。因此,克莱因说,在本能的压力下,存在着对某些刺激作出反应而不对其他刺激作出反应的准备,这种准备被比昂(1962,1965)称为 "预想"。最后,最近的研究结果指出产前大脑活动的存在(Mancia, 1981; Ploye, 1975; Verney & Kelly, 1981),可能与母亲的情绪状态有关(Ferreira, 1965)。

总之,尽管在自闭症/粘附性识别阶段还没有一个能 "思考 "的头脑,但很可能存在着心理(定义为模糊的生理事件)内容。这种内容可能来自几个方面:作为本能的一个维度的先入之见,产前经验的残余,以及对实际心理生理事件的幻觉再现。这一时期的心理内容被认为是具体的,因为不存在从经验事件中提取意义的思想。向知觉/感官模式倒退的地形学上的不确定性是植根于这个发展水平的。此外,这一阶段的心理内容是为了实现同质平衡,在本讨论中被称为自闭症对象。Tustin (1972, 1980)提到自闭症儿童使用的 "硬的"物体,其部分功能是为儿童提供一些象征性的依靠,以代替足够的皮肤边界。因此,自闭症或硬物是心理内容的最早形式,就其服务于平衡的目的而言是具体的,并由知觉/感官事件组成。
从出生后第二个月到五个月左右,婴儿与母亲形成共生关系(马勒,1975年),并通过 "驱逐现象 "来保护自己免受内部紧张的影响,将不愉快散布在共生轨道之外。因此,马勒在共生阶段的心智模型是一个驱逐性的器官,其内容基本上是以生理学的方式定义的(快乐/不快乐)。与马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皮亚杰和克莱因描绘的是一个已经开始积极地(尽管是微弱地)塑造其世界的婴儿。皮亚杰(1952年,1954年)将婴儿描绘成故意和重复地对其环境采取行动,婴儿在制造事情中获得快乐。皮亚杰和克莱因断言,外部世界是根据内部经验,通过同化适应(皮亚杰)或通过正常的投射性认同(Bion,1959;克莱因,1946,1952,1957),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感知。这些作者共享的内隐心智模型是一种肌肉模型,其特点是心理内容的投射(马勒、克莱因、皮亚杰),对重复行动模式的严重依赖(皮亚杰),以及一种主动 "塑造 "环境以匹配内部状态(克莱因、皮亚杰)。婴儿享受着每次睁开眼睛时全能地创造环境的幻觉(温尼科特,1953)。
为了使心理内容不那么具体地被思考,必须存在一个认知装置,它不仅仅通过驱逐来 "思考"。此外,必须有一个隐喻性的 "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精神内容可以被思考。随着自闭症/粘附性识别早期阶段的成功解决,一个受皮肤限制的内在空间被建立起来;然而,在共生/偏执分裂阶段,这个空间与母亲的空间是共存的。温尼科特(1971)将这种缺乏分化的时间称为 "潜在空间",表明随着母亲和婴儿之间开始发生分离,他们之间增长了一个隐喻性的区域,游戏和想象性思维可以发展。只要这个空间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孩子的思维就不能实现扩展,只是等同于母亲的思维。

婴儿的认知过程Bion(1962)对此进行了精确的阐述,他认为婴儿的认知过程依赖于其母亲的认知过程。正常的投射性认同(Bion, 1959; Grotstein, 1980)将母亲和婴儿共享的某些经验放入集体空间,这些经验既有愉快的,也有不愉快的(Brown, 1980),这些经验来自婴儿体内。然后这些投射的元素通过母亲的认知过程(根据Bion,她的 "遐想 "能力)转化为有意义的事件(Bion,1965),这样,在直接的具体经验之外没有意义的知觉/感官经验(β元素)开始积累意义(α元素)。β元素只适合于通过投射性认同或见诸行动来释放,而α元素则能够被思考。然而,在这一发展阶段,只有一个从感知/感官事件到内部经验的新生转变,这种转变正在积累心理学意义,与母亲的α功能的共生联系允许向后来出现的抽象思维进一步发展。
对于考虑思维机制和思维发生的空间而言,对具体性的研究同样重要的是所思考的精神内容的性质。共生/偏执阶段的心理图像反映出其在人际间领域中缺乏区别性。在这个阶段的表象可能最好被描述为共生的客体。由于投射/同化过程占据主要位置,自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客体的表征是具体的,因为它们并不象征性地代表客体,而是被认为等同于客体(Segal, 1957, 1978)。在讨论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抽象或隐喻思维的发展时,Rosenfeld(1955)和Searles(1962)都注意到,随着自体和客体分化的增加,具体思维也在减少。
符号学的具体性是从自我和非我之间的界限不明确的客体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并与之相关。这种界限的缺失导致了无法区分符号和它所象征的东西。皮亚杰(1945年)将无法区分内部参照物和外部客体(他的 "自我中心 "概念中所包含的)与区分符号者和被符号者的缺陷联系在一起。在使用罗夏墨迹测验的研究中,一些作者(Athey, 1973; Blatt & Ritzier, 1974; Blatt & Wild, 1976; Blatt, Wild, & Ritzier, 1975; Sugarman, 1980)将墨迹的形状与自我和客体不分的临床表现相提并论。此外,格林斯潘(1979)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混合与共生的困难联系起来。因此,符号学的具体化应该被看作是在整体概念和人际关系模糊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共生客体的构成中固有的。

这里采用了共生客体的说法,而其他人则用不同的名称来描述类似的心理表征。克莱因学派使用内部客体这个属于来暗指这种现象,肯伯格(1975,1976)提到 "无差别的自我客体表征"。温尼科特(1971)和Deri(1972)则使用术语 "原型符号 "来注意反映自我和客体之间缺乏区分的心理表征。这里使用共生客体指代具体性,也意味着对这种内部内容具有的主观意识。因此,在这个阶段 "思考"的心智模式是肌肉记忆型的,与此相应的是"思考"的体验的重要性。因此,感到被内心体验压垮或压迫,因为它们没有超越眼前体验的意义,严重退行的人将通过肌肉 "思考"(投射性认同)或通过肌肉组织(见诸行动)来摆脱这种 "想法"。
总之,具体性与共生/偏执分裂阶段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地形上的具体性蕴含在一个具体的过程中,如果母亲能够共情和转化婴儿内部状态,这样的一个形象会为婴儿的感知/感觉内容产生意义。此外,用行动/释放模式代替“思考”,而不是有一个能够自行反映和转化经验的头脑。符号学的具体化反映了这一阶段的人际关系氛围,其中自我和他人的界限是模糊的。最后,一个可以思考心理内容的空间或头脑在婴儿体内还没有完全分化,所以孩子的认知能力仍然具体地依附于在母亲的能力上。
在这个发展阶段,横跨大约5个月到15或16个月的时期,在孩子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观察到快速的增长。根据马勒(1968年,1975年),在分离-个体分化阶段的第一个子阶段,婴儿正从与母亲的共生外壳中 "孵化 "出来。孩子正在发现这个世界,注意到物体和人,并尝试着独立。然而,在联系身体上独立于母亲的同时,和母亲保持视觉上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与母亲的分离变得不那么受伤,孩子才能逐渐发展出兴奋的探索行为。
Parens(1979年)在对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进行仔细的观察研究时,观察到孩子在出生后第一年的最后一半时间里攻击性急剧上升,并证明了分离-个体化过程是如何被增加的攻击性驱动所鼓励的。马勒和Parens都注意到这一时期自我功能的快速增长,但没有具体涉及认知发展。
克莱因(1946,1952,1957)提出了她的观点,即儿童已经进入了抑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整合客体的内部图像的能力已经存在。克莱因认为,形成符号的能力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小孩子使用这种所谓的符号来帮助处理围绕损失的冲突。这种观点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关于维持母性客体的复杂和综合心理形象的能力出现的时间有很多讨论(Fraiberg, 1969; Hartmann, 1952; Mahler, 1975; Spitz, 1957)。然而,具体说明儿童何时可以获得客体的独特表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追踪实现这一终点的过程(Bowlby, 1980)。

在其他作品中(Brown, 1984, 1985),我曾提出了一个介于克莱因的偏执精神分裂位态和抑郁位态之间的中间或过渡位态,部分是为了帮助纠正她对形成符号的认知能力的错误判断(Groh, 1980)。此外,过渡位态的概念有助于将她的工作与皮亚杰和温尼科特的观察相结合。在过渡位态上,自我与客体有一个缓慢的分化,这也是共生/偏执分裂阶段中共生客体的特点。主体和客体正在脱离混乱和生活在相同空间的状态,现在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重叠的空间。重叠的程度将随着成功分离的发生而减弱,直到第二年中期实现自我和非自我的完全区分,这时达到马勒的和谐阶段和抑郁位态本身。温尼科特(1953)关于过渡性物体的观点最能说明过渡位态的心理表征。过渡性客体有助于弥合自我和客体模糊的共生过去与体验分离现实的未来。在本文所概述的心理表征的发展过程中,过渡性客体是从共生客体发展而来的,而共生客体的前身是自闭症客体。
就象征性地表征客体的能力而言,过渡性客体还不是一个符号,因为它同时代表了儿童和母亲(Winnicott, 1953)。Deri (1972)说,过渡性客体站在原型符号和真正的符号之间。Blum(1978)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补充说符号表征意味着符号者和被符号者之间的区别。就符号学的具体性而言,过渡性客体是为增加词和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服务的。与过渡性客体相对应的是罗夏克(Rorschach),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同的概念被不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如 "一个长着鸟的翅膀的人",然而,这两个概念并不像墨迹那样是完全模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一个概念边界被破坏的共生对象的世界里,而边缘患者则沉浸在边界脆弱和不明确的过渡性位置上。边缘型病人的罗夏记录经常以捏造的组合(Rapaport, Gill, & Schafer, 1968; Singer, 1977)和距离的丧失(Sugarman, 1980)为特征,其中病人的内部过程和对墨迹的反应的通常分离变得暂时模糊了。
这里的过渡性客体与温尼科特(1953)的用法不同,后者指的是实际可触及的 "非我的所有物",如一条毯子,并不强调其内部所指。这里建议的用法是为了对充温尼科特的概念有所补充,是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心理表征,在这种表征中,自我和非自我还没有被区分,也没有完全分开。从克莱因理论的角度来看,除了已经描述过的共生客体之外,过渡性客体是另一类内部对象。按照这里的定义,过渡性客体与Coen(1981)所说的 "产前客体"、Kernberg(1966)使用的 "非代谢 "自我状态以及Kohut(1971, 1977)的自我客体概念同义。

从地形具体化的角度来看,过渡性客体可以被看作是儿童认知功能的产物,它越来越有能力在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它对环境的假设。根据皮亚杰的理论(1952年,1954年),儿童的自我中心开始屈服于现实的要求,观察者现在可以注意到适应的早期迹象,通过这些迹象,内部印象越来越受到现实的影响。因此,过渡性客体提供了一个从同化适应到调适适应的桥梁(Deri,1972),也可以被认为是初级和次级过程思维之间的中介。对母亲的α功能的认同允许使用这个过渡性空间,这个空间随着共生关系的消退而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发展,作为尝试新的认知形式的舞台。孩子在出生后第二年的前半部分可以获得基本的概念,在这方面,随着孩子能够对其经验赋予意义,地形的具体性就会减弱。这样的早期概念仍然与行动模式和文字-声音的神奇力量联系在一起。心理内容往往具有 "重量",因为符号和它所象征的东西是部分融合的,而且 "过渡性幻想"(Volkan, 1976)可以被当作是心灵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召唤的有形经验来抚慰自己。
在分化和实践的过渡位置上,"思考 "的技术也在不断复杂化。费尔贝恩(1952年)描述了一个 "过渡阶段",与本节讨论的时期相吻合,并概述了作为应对冲突的手段而出现的一些高级手法(恐惧症、偏执狂、强迫症和癔症)。在不详述这些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快速成熟的认知手段的观察与皮亚杰关于此时儿童适应能力扩大的发现相吻合。作为对这些研究的补充,Roiphe和Galenson(1981)也注意到,到了第二年开始,相对复杂的游戏模式初步出现,可以用于防御。然而,行动/发泄模式仍然是消解内部紧张的主要模式。
总之,在过渡/分化和实践阶段,可以注意到代表物体的能力比操纵这种内部形象的认知策略的变化更大。换句话说,儿童对其经验进行概念化、区分和理解的能力比其 "思考"、应对和适应的能力要强。过渡位置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从共生到分离,从符号学的具体性到抽象和意义,从可能通过行动/发泄的方式到适合于经验的语言表述的思想。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困在一种虚弱的精神状态中,被要被驱逐或被幻觉的共生对象的重量所困扰,而边缘的病人则与过渡性客体打交道,这些客体把他诱导到真正意义的边缘,但使他无法从他的经验中学习。
这个发展阶段从大约15或16个月到出生后的第三年,以儿童意识到其与母亲的实际分离为标志。根据马勒(1968,1975)的说法,幼儿的个体化在实践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幼儿的行为是自主的,但是他们仍觉得与母亲客体是一个整体。然而,被解释为儿童没有体验到自己是独立的,可能也与地形的具体化状态有关,在这种状态下,分离的数据(对与母亲的距离的感知,通过行动的独立)对幼儿来说还没有什么意义,随着和解危机的开始,儿童开始面对其自主行动的意义。因此,和解危机是由不可避免的分离和个体化的成长召唤出来的,但也是由认知装置的某种自主成熟召唤出来的,它允许分离的经验数据在概念上被登记为 "我是(可怕的)分离的"。
儿童认知能力的这种自主成熟与儿童独立空间的建立相辅相成。在以前的过渡性位置,孩子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叠的空间,其特点是对母亲的α功能的依赖减少,尽管其体验上仍然很重要。现在,在抑郁症的适当位置/和解阶段,或多或少的完整分离状态正式确定了内在空间的界限,在这个空间里,儿童的头脑,用它自己的α功能武装起来,这些功能部分来自认同。以这种方式,成熟的力量(皮亚杰)与走向分离-独立的运动(马哈蒂尔)交织在一起。分离--个体化(马勒)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后者与独立思考的头脑所在的内部空间的划分有关(温尼科特)。
地形的具体性被幼儿对其经历的事件进行反思的新生能力所削弱,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开始出现,从而使头脑不再对事物进行字面理解,更加复杂的游戏为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而出现(Deri, 1972; Piaget, 1945; Roiphe & Galenson, 1981; Winnicott, 1971) 。此外,地形复杂性的减弱是认知功能整体成熟的一部分,包括更高层次的防御机制的发展,如压抑、反应形成和心智化(Kernberg, 1970)。原始的防御机制,如投射性认同和全能性的否认与思维的肌肉模型相关,这部分从心理内容中被排除或挤压出去,更加成熟的防御使得一些心理内容被聪明地隐藏、掩盖或者被解释为不存在,目的是为了不丧失掉其中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地形的具体性与更高级的思维形式相关联,这些思维形式出现在适当的抑郁位态/和解阶段。

但是,以这些更先进的方式思考的精神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符号的形成,它们重新呈现或代表了客体。在这方面,符号者和被符号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含的距离,在这种距离中,关联性将两者联系起来。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东西不再需要分享那么多共同的品质(Roiphe & Galenson, 1981)。我建议对这个阶段的心理内容使用客体(或自体)表征一词,在这个阶段,符号者和被符号者是分离的。客体表征是心理内容从自闭到共生到过渡性客体的最后阶段。
物体表征中的符号者和被符号者之间的分离是由儿童和母亲在这个阶段的成功分离而实现的(Brown, 1984)。只要接受分离的现实所固有的冲突在人际关系领域没有被克服,持久的客体表征的形成就不会在认知领域出现。在几个因素中,马勒(1975)强调了母亲在和解阶段的重要性,即支持幼儿走向自主的过程,并接受儿童对持续依赖的需求。随着这一危机的成功解决,一个稳定的内部化的母亲形象和综合的自我表象得以实现(Kernberg, 1966, 1975, 1976)。
克莱因学派(Klein, 1930, 1952, 1957; Segal, 1957, 1978)也强调了接受与客体分离对符号形成发展的重要性。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克莱因将抑郁症位态的象征能力的出现放在第一年末,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儿童发展实证的支持;因此,这一阶段建议称作过渡性位置。因此,本节所涉及的进入第三年的15或16个月的时期将被称为抑郁位态,在这个位态上,如果对母亲有过度的攻击性,则会失去一个完整的母亲。处理抑郁性焦虑的退行性手段就是回到原始防御并保持在过渡位置(Brown,1980;Steiner,1979);然而,还有一种新的适应方式是形成一个象征,其可以代表外部的母亲,但实际上只存在于内部。原始的防御机制,如投射性认同,会加强象征的具体性,并创造了象征的等式,在这其中自我和客体被部分的认同。当分离状态可以被容忍和接受时,真正的符号形成(客体表征)就会进行,符号学的具体性也随之减少。
总而言之,适当抑郁位态/和解阶段是一个人际关系和成熟因素相结合的时期,说明了超越符号学和地形学具体性的能力。当自主认知的成熟与儿童成功地认同了母亲的阿尔法功能时,概念的发展就会在儿童身上进行,而这种功能现在被认为是存在于幼儿的内部心灵空间中,与母亲分离。这导致了地形的具体化和用于适应和防御目的的更高级的认知策略的减弱。此外,随着分离被容忍和接受,心理内容的发展,自我和客体或符号者和被符号者被明显地区分开来。这样的心理内容被称为客体(和自我)表征,以区别于自我和客体分离程度不完整或不存在的共生和过渡性客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重点一直放在地形学和符号学具体性的根源上,却很少提到互动的具体性。如上所述:"互动具体化的病人没有表现出器质性、思想混乱的外在迹象,他们的字面意思不能用器质性、地形学或符号学具体化来解释"。这些病人尽管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抽象能力,但可能显得很密集,无法把握分析师的干预的含义。分析探索一般会发现,这种干扰与按照病人的冲突进行解释的无意识经验有关(Racker, 1968)。因此,病人可能不接受或不理解,或者对干预的预期意义感到紧张。
举例来说,有一位女性患者,在与她有婚外情的已婚男子决定停止他们的关系后,因抑郁症寻求心理治疗。她说对方非常支持她,并说他 "把我拉在一起"。她对前情人的联想可以追溯到她的父亲,她回忆起在她母亲去世后,她在5到7岁时曾与父亲有过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光。病人表现出出色的抽象能力,与她现在的失望和她七岁时父亲再婚时的排斥感之间做了许多相似之处的描述。在一次治疗中,我宣布我将离开一个星期,病人开玩笑地回答说她的安全毯会消失。在下一次治疗中,病人描述了自己无法思考的情况:她的想法很分散,没有方向。我最初解释了她对我即将离开的焦虑,但我的评论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听起来像是没有意义的话语。
我开始认为,她所经历的思想混乱其实是她觉得自己没有一个能把它们凝聚在一起的头脑的一种表达。在这方面,她的头脑无意识地被体验为无法将她凝聚在一起的父亲/治疗师,而她分散的想法表达了她的主观体验,即她是一个需要被凝聚在一起的小而惊恐的孩子。因此,我之前的干预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解决她头脑中不能抽象思考的当下的性质。我再次解释说,我即将到来的缺席被认为是对支撑她的东西的移除,她的头脑现在被体验到像我对她一样无用。因此,我继续说,她的思想是分散的,似乎在要求我用语言来概括它们。病人仍然显得有些困惑,但随后想起她曾经坐在她父亲的腿上,感觉被他的怀抱包裹着。疗程结束后,在下一次回来时,她说她的思想恢复了正常。
在这个例子中,互动的具体化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症状发生了,因为我的干预被无意识地认为是像筛子一样的,无法将她的 "散乱 "状况固定下来。另一种可以观察到互动性具体化的情况是,病人的联想很平淡,似乎没有什么衍生的意义。这种临床情况被Langs(1978a, 1978b)称为C型交流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言语会破坏治疗互动的意义。C型叙述者 "必须断绝与分析者的任何情感联系,以便通过保持互动的具体性来避免强烈的痛苦材料的出现(Giovacchini, 1972, 1979)。C型叙述者的互动性具体化可能代表了一层薄薄的表皮,覆盖了符号学或地形学具体化的强烈倾向。换句话说,他们的密集性和字面性形成了一个防御屏障,以抵御以共生和过渡性客体为主的潜在精神生活的出现(Brown, 1984)。

在神经症患者中,存在着客体关系冲突的激活,这些冲突被无意识地储存为客体和自我表征(正如本文所定义的那样)。因此,这类病人的移情通常不涉及自我和客体区分的困难。此外,他们的联想通常带有潜在的意义,这是由用于交流的词语或符号重新呈现被符号化的内部状态这一事实促成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概念界限以及词和它所指的情感之间的概念界限是明确的,分析家的任务是将言语与病人的联想重新呈现的无意识状态联系起来。然而,许多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特别是在人格的精神病部分活跃的退行期(Bion,1975;Brown,1980;Grotstein,1977a,1977b),失去了以衍生方式交流的能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临床情况的特点是倒退到一个具体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心灵以肌肉的方式工作,以驱逐精神内容(共生和过渡客体)。
当自我和客体之间的分界变得模糊,词语则可能被体验为等同于它们所要表达的东西,概念的界限可能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的任务是 "容纳"(Bion, 1962; Langs, 1978a, 1978b)病人的投射性认同,通过使这些投射受制于他自己的阿尔法功能而赋予它们意义,并通过这个过程使被投射的东西充分地 "解毒",使病人能够重新进入投射过程。
在C型叙述者的情况下,互动的具体性有助于防止出现更不祥的地形和符号学的具体性,这往往是退行性临床状态的特征。
诊断交互性具体性的性质以及心理表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Brown, 1984)。如果互动的具体性是病人与解释的关系的结果,就像上面描述的那位妇女一样,那么病人表现出的密集性可能无法抵御更原始的转移材料的激活。然而,C型叙述者的互动的具体性可以防止潜在的灾难性痛苦的情感状态的进入,这些情感状态是具体地体验和具体地 "思考 "的。如果诊断出互动的具体性属于C型叙述者的范畴,那么临床医生还必须评估心理表征的性质(共生的或过渡客体),当病人的笼统和字面的障碍被揭开时,这些表征可能在移情中被激活。不同的临床状态就会出现,这取决于治疗环境中共生性或过渡性客体是否被激活。下面的小片段说明了在一个采用C型交流模式的病人身上出现了过渡性客体的心理表征,同时也说明了这种风格与感觉被这类病人欺负的常见反移情之间的关系。

一位边缘型女性进入心理治疗,试图从她多年的慢性抑郁症中找到解脱。她见过很多治疗师,通过各种方式接受 "治疗",在进入我的治疗之前,她已经得到了一些暂时的缓解,一位精神病医生解释说,她患有生化失衡,可以通过锂和抗抑郁药物治疗来纠正。尽管她继续使用药物治疗,但这种从她通常的苦闷抑郁状态中得到的喘息是短暂的,可能与她从进入心理治疗的计划中获得的短暂希望有关(Langs,1982)。她决定进入高强度的心理治疗,与其说是与她希望获得有意义的理解有关,不如说是代表了另一种尚未被尝试的模式。
在许多次治疗中,病人以一种情感疏离的方式谈论一些话题,她的联想很稀少,而且她反复重复同样的材料。对于有关她的症状的心理意义的建议,病人不断地反驳说,她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是一种生理疾病的受害者,只能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病人开始质疑心理治疗的价值,这种抱怨与我的厌烦感不谋而合。我干预并指出,她遭受生理疾病的概念吸引了她的一部分希望,使得她认为她的痛苦没有意义。我继续说,她希望使她的长期痛苦没有意义的那部分,现在正在工作,不让她谈论她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也不让她通过我们深入探讨她深层的情感而感到与我有联系。我的干预立即引起了她的仇恨,因为接下来我被指责为不理解像她这样被抑郁症困扰的精神病人的困境。我怎么能理解她的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 "精神病人",她要求我这样做,暗示她想让我感受她的抑郁症。她在会话中早些时候的互动性具体化已经让位于与我的实际的、虽然令人不安的、愤怒的联系。这种与我的联系是一种行动/释放的交流模式,它被用来通过投射性地将情感(感觉)状态认同到我的身上来摆脱它。
我最初的无聊感很快就被一种被欺负的体验所取代。当她对我大发雷霆时,我产生了一个视觉幻想:一个人被另一个咄咄逼人的问话者反复推到墙上,他的手臂愤怒地伸出来。在这方面,我的认知功能也倒退到了一种地形上的具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与病人的关系是以感知的方式来体验的。现在我要从与病人的互动中转移一下注意力,因此此处引入关于投射性认同的一些评论似乎是必要的。我被欺负的感觉显然与病人使用暴力的(Bion, 1959)投射性认同有关,也反映了病人的地形具体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她的抑郁症,被她觉得是一个无意义的具体感觉事件,只能以肌肉的方式被 "思考"(投射性认同)。

因此,对投射性认同的完整研究(Grotstein, 1980)还应该包括对被投射的心理内容的具体性的考虑。最后,投射性认同还包括寻找一个 "容器",这个容器可以接纳具体经验的投射物,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较低的具体性状态,以便可以对其进行有意义的思考(二级过程)。因此,投射性认同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心灵的绝望行为,它只能以肌肉的方式摆脱具体经验的精神内容,但也是对分析师的恳求,希望其可以赋予意义。
本文描述了具体性的子类型(器质的、地形的、符号的和互动的)。这些都是在生命的头两年半的整体发展背景下考虑的,认知的增长与客体关系的成熟有系统的联系。有助于具体化的因素是可用于思考的认知策略的性质、独立运作的头脑所在的内部空间的成长以及自我和非自我的逐渐分离。最后,我们提供了一些临床实践中具体性的例子,特别是与投射性认同的性质有关的例子。
参考文献
Arieti, S. (1974) Interpretation of Schizophrenia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Arieti, S. (1976) Creativity: The Magic Synthe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Athey, G. (1974) Schizophrenic Thought Organization, Object Relations, and the Rorschach Test. Bull. Mennin. Clinic., 38: 406-429.
Bick, E. (1968) The Experience of the Skin in Early Object Relations. Int. J. Psycho-Anal., 49: 484-486.
Bion, W. (1957)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sychotic from the Non-psychotic Personalities. Int. J. Psycho-Anal., 38: 266-275.
Bion, W. (1959) Attacks on Linking, Int. J. Psycho-Anal., 40: 308-315.
Bion, W. (1962)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Heinemann.
Bion, W. (1965) Transformations. London: Heinemann.
Blatt, S., Brenneis, C., Schimek, J., & Glick, M. (1976) Norm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on the Rorschach. J. Abnorm. Psychol., 85: 364-373.
Blatt, S., & Ritzler, B. (1974) Thought Disorder and Boundary Disturbances in Psychosis. J. Consul. Clin. Psychol., 42: 370-381.
Blatt, S., Wild, C., & Ritzler, B. (1975) Disturbances in Object Representations in Schizophrenia. In D.
Spence (Ed.), Psycho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Vol. 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Blatt, S., & Wild, C. (1976) Schizophrenia: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lum, H. (1978) Symbolic Processes and Symbol Formation. Int. J. Psycho- Anal., 59: 455-471.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III: Loss. New York: Basic Books.
Brown, L. J. (1980)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the Depressive Posi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rown, L. J. (1984) Level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ve Modes of the Bipersonal Field. Int. J. Psycho-Anal., 10: 403-428.
Brown, L. J. (1985) The Transitional Position.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Coen, S. (1981) Notes on the Concepts of Selfobjects and Preoedipal Object.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29: 395-411.
Deri, S. (1972) Transitional Phenomena: Vicissitudes of Symbolization and Creativity. In S. Grolnick, L. Barkin, & W. Muensterberger (Eds.), Between Reality and Fantasy. New York: Jason Aronson.
Fairbairn, W. R. D. (1952) An Object-Relations Theory of the Person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Federn, P. (1952)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Fenichel, O. (1945)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New York: W. W. Norton.
Ferenczi, S. (1913)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Sex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bert Brunner, 1950.
Ferreira, A., (1965) Emotional Factors in Prenatal Environment. J. New. Ment. Dis., 141: 108-117.
Fleiss, R. (1959) On the Nature of Human Though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Dream and Other Psychic Productions. In M. Levitt (Ed.), Readings in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Fraiberg, S. (1969) Libidinal Object Constancy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 Psychoanal. St. Child, 24: 9-47.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4 & 5, 1953.
Freud, S. (1915a) The Unconscious. Standard Edition, 14: 66-215, 1957.
Freud, S. (1915b)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Standard Edition, 14: 111-140, 1957.
Freud, S. (1923) The Ego and the Id. Standard Edition, 19: 13-66, 1961.
Giovacchini, P. (1972) The Concrete and Difficult Patient. In P. Giovacchini (Ed.), Tactics and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Vol. 1). New York: Jason Aronson.
Giovacchini, P. (1979) Treatment of Primitive Mental State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Goldstein, K. (1939) The Organism. New York: American Book.
Greenspan, S. (1979) Intelligence and Adaptation. Psychol. Issues, 12: 314.
Groh, L. (1980) Primitive Defenses: Cognitive Aspects and Therapeutic Handling. Int. J. Psycho-Anal., 8: 661-683.
Grotstein, J. (1977a)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 I. The Dilemma. Int. J. Psycho-Anal., 58: 403-425.
Grotstein, J. (1977b)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 II. Reconciliation. Int. J. Psycho-Anal., 58: 427-452.
Grotstein, J. (1979)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 of the Borderline Organization. In J. Le- Boit, & A. Capponi, (Eds.), Advances in Psychotherapy of the Borderline Patient. New York: Jason Aronson.
Grotstein, J. (1980) Splitting and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New York: Jason Aronson.
Hartmann, H. (1952) 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 In Essays on Ego Psych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4, pp. 155-182.
Jacobson, E. (1964) The Self and the Object Worl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ernberg, O. (1966) Structural Derivatives of Object Relationships. Int. J. Psycho-Anal., 47: 236-253.
Jacobson, E. (1970) A Psychoanalytic Classification of Character Pathology.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18: 800-822.
Jacobson, E. (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Jason Aronson. Jacobson, E. (1976)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Klein, M. (1930) The Importance of Symbol 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In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1921-1945.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8, pp. 282-310.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 J. Psycho-Anal., 27: 99-110.
Klein, M. (1952) 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 In Envy and Gratitude.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5, pp. 61-93.
Klein, M. (1957) Envy and Gratitude. In Envy and Gratitude,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5, pp. 176-235.
Kohut, H. (1971)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Langs, R. (1978a) The Listening Proces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Langs, R. (1978b) Some Communicative Properties of the Bipersonal Field. Int. J. Psycho-Anal., 7: 89-135.
Kohut, H. (1982) The Psychotherapeutic Conspiracy. New York: Jason Aronson.
Mahler, M. (1968) On Human Symbiosi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Individuation, Vol. 1, Infantile Psycho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Mahler, M., Pine, P., & Bergman, A. (1975) 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the Human Infant. New York: Basic Books.
Mancia, M. (1981) On the Beginning of Mental Life in the Fetus. Int. J. Psycho-Anal., 62: 351-357.
Meltzer, D. (1975) Adhesive Identification. Contemp. Psychoanal, 11: 289- 310.
Parens, H.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on in Early Childhood. New York: Jason Aronson. Piacet, J. (1945) 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 New York: W. W. Norton.
Piacet, J. (1952) The Origin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Piacet, J. (1954)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d the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Ploye, P. (1975) Does Prenatal Mental Life Exist? Int. J. Psycho-Anal., 56: 107-118.
Racker, H. (1968)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Rapaport, D., Gill, M., & Schaeer, R. (1968) Diagnostic Psychological Testing (Rev. e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Roiphe, H., & Galenson, E. (1981) Infantile Origins of Sexual Identi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Rosenfeld, H. (1955) Notes 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Superego Conflict in an Acute Schizophrenic Patient. In M. Klein, P. Heimann, R. Money-Kyrle (Eds.), 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 London: Tavistock.
Searles, H. (1962)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ncrete and Metaphorical Thinking in the Recovering Schizophrenic.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10: 22-49.
Searles, H. (1967) The Schizophrenic Individual's Experience of His World. Psychiatry, 30: 119-131. Segal, H. (1957) Notes on Symbol Formation. Int. J. Psycho-Anal., 38: 391- 397.
Segal, H. (1978) On Symbolism. Int. J. Psycho-Anal., 59: 315-319.
Singer, H. (1977) The Borderline Diagnosis and Psychological Tests: Review and Research. In P. Hartocollis (E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Spitz, R. (1957) No and Yes: On the Genesi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Steiner, J. (1979) The Border between the Paranoid-schizoid and the Depressive Positions in the Borderline Patient. Brit. J. Med. Psychol., 52: 385-391.
Storch, A. (1924) The Primitive Archaic Forms of Inner Experiences and Thought in Schizophrenics.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cation Company.
Sugarman, A. (1980) The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as Manifested on Psychological Tests. In J. Kwawer, H. Lerner, P. Lerner, & A. Sugarman (Eds.), Borderline Phenomena and the Rorschach Tes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Tustin, F. (1972) Autism and Childhood Psychosis. Science House, Inc. Tustin, F. (1980) Autistic Objects. Int. Rev. Psycho-Anal., 7: 27-40.
Verny, T., & Kelly, J. (1981) The Secret Life of the Unborn Child. New York: Summit Books. Volkan, V. (1976) Primitive Internalized Object Rela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Werner, H. (1957)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Men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Winnicott, D. W. (1953)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 Int. J. Psycho-Anal., 34: 89-97.
Winnicott, D. W.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