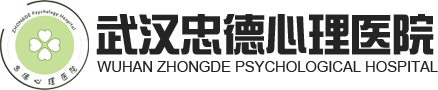作者认为解释工作是一个连续的诊断过程,其中分析师同时使用了情感和智力活动。在本文中,她讨论了进行解释时分析师心目中的三个基本因素:“什么”,“何处”和“何时”。她在“什么”中谈到移情关系是解释的核心。她将移情理解为过去内部客体关系的一种表达,由于某种原因该内部客体关系无法发展,并且会重复特定的影响,在患者和分析师的关系中出现焦虑和防御。“何处”的概念是检查患者感觉到问题出在哪里:是在分析者那还是在他本人这里。这取决于患者的功能水平。如果他主要在偏执-分裂的水平上运作,投射机制的使用将是相当多的,并且解释应该集中在分析师身上。当功能模式主要对应于抑郁位置时,患者会感觉到自己的问题;因此,解释应该以他为中心。最后,在“何时”中,作者陈述了有助于分析师将患者交流的不同要素整合到新公式中的因素。完整报告了患者分析的整个过程,并将其用于说明和讨论本文所支持的观点。
解释是分析工作的核心。在分析中,分析师倾听并尝试感受患者的话语,观察他的讲话方式、使用的语言、(对他)惯常和不寻常的表情、情绪语调以及患者的动作、 姿势、神态的改变;可以说任何能够观察到的东西。
分析师也观察他自己的反应,以及患者在他身上引起的感觉,并试图找到哪些来自他自己,哪些是患者动力的直接表达。使用所有这些材料,他不仅对患者和他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将此呈现给患者作为解释。解释性工作是一项持续的诊断活动,旨在就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发生的情况达成假设。分析师希望这些假设能够以某种方式影响患者,最好以产生洞察力并促进进一步分析理解的方式。为了继续进行分析工作,分析师必须观察患者的所有反应,无论他们是否富有洞察力,以便能够评估其解释所带来的处境,然后在他的脑海中制定新的、最终他能给到患者的解释。
因此,解释性工作是情感和智力活动的混合体,这两部分必须同时存在。分析师对患者的情感理解必须经过思维处理,以使他能够形成解释。

在本文中,我想谈谈三个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分析师进行解释时所构想的框架。我希望在以后澄清一下,我要说的是在分析师对患者提出解释之前,该材料是如何在分析师的脑海中形成的。
对于我将谈到的移情关系中的“什么”,我将其理解为患者内部世界的一种表达;就是说,患者与他的分析师之间的当前关系是过去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发展的内部客体关系的表达。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何”事情的表达正如它们在分析中所做的,而这也构成了“什么”的一部分。
对于“何处”,我将指的是患者的功能水平,尤其是在偏执分裂位与抑郁性位(PS-D)之间的运动中反映出来的水平,这种运动导致以投射性还是内摄性过程为优势。过度的投射会导致患者感觉到移情所表达的情境的原因和责任在于分析师。投射的减少和内摄活动的增加使患者认识到并最终为自己的感觉负责。分析师对这种情况的评估将决定解释的方向。
最后,在 “何时” 中,我将讨论帮助分析师在给定时间将患者沟通的不同元素整合到一个新的公式中的因素,然后可以用语言表达给患者。我想澄清的是,我指的不是通常所说的解释的“时机”(即应该在什么时候对患者说),而是分析师头脑中某件事以某种特定方式结合在一起时的活动。
“什么”、“何时”、“何处”是每一种解释的形成因素,因此对分析的发展至关重要。大多数分析师会感性地感知到发生了什么,但每个分析师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论背景来理解这一点。是我们的理论让我们理解患者的材料,并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向他解释。例如,一些分析师认为,分析中最重要的工作是重建患者的过去。我的观点非常不同。我相信患者早期的冲突(还没有演成更成熟的状态)仍然在他的脑海中存在,并在当下的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关系中表达着。因此,我的重点将是解释移情。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观点更接近于 Sandler 关于他们所谓的“当下无意识”的观点,也就是说,患者的那些无意识的表达是可用的,只有在此时此地的分析会话中才能被触及。

我的立场也不同于那些认为解释发生在咨询室外的移情可能会使咨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分析师们:也就是说,对于患者在分析中对关系和情景所叙述的解释应在“那时那地”,即分析师的解释要与它们在何时何地发生相关。我认为,患者的心理运作和结构的变化主要是通过移情情境中的“此时此地”的生活经验来实现的,因此,使这一点成为中心,而不忽视和整合患者的外部生活与他过去的历史。
我相信所有的分析师都会做出与患者的生活(过去和现在)相关的移情解释,但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将取决于根植在每个人心里的心理理论,这是他们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
现在我将讨论这篇文章的主题,并试着澄清我根据临床材料列出的每一点与我使用的理论联系起来。
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位患者 A 女士的情况,当时她已经和我一起分析了约5年。她来自一个北欧国家,在与丈夫结婚并移居英国之前,她在那里接受心理分析。她年近三十,有三个孩子。

A太太是六个孩子中的第四个,他们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她有一个兄弟住在意大利,其他的同胞则留在原籍国。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家庭,她经常在周末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有时他们一起度过假期。从青春期晚期开始直到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她都有着严重的暴食症。她经常暴饮暴食,使自己呕吐。(她至少每天吐一次,但更多的是每天好几次。)在分析开始时,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她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体重,从不丢失或增加一克。她反对暴食症这个词,她自己的表达是“进食和呕吐”。
A太太很聪明,受过教育也有教养。她有很好的爱的能力,但也有非常敌对和嫉妒的倾向。多年来在分析中她一直非常保护她的母亲,在移情关系中母亲浮现出了关爱的特质——也许是被这么多的孩子淹没了,而不是因为太忙而不可触及。自从孩提时代起,她就对父亲非常敌对,但最近他开始以不同的形象出现,让她对他更友好。她的嫉妒感非常强烈,尤其是针对她的大姐姐和小同胞。她和哥哥汤姆(现在住在意大利)有过一段艰难的、有些不正当的性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又出现了。
起初,她在分析中如鱼得水,带来了大量的梦,而且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是,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在她的咨询中我经常感到困倦并且有些无聊。我喜欢她且从不觉得我想让她不来,但是在咨询的过程中我常常发现自己的思想在游走。慢慢地,我意识到咨询中保持着微妙而又非常严格的控制,因此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解释似乎已被接受,但很快被部分地推出。她似乎觉得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她试图在分析中采取她在生活中通过饮食和呕吐形成的同样的办法(到目前为止,这被理解为旨在维持某种平衡的控制的一种表现)。有很多的联想和梦境,但她说话的语气却有种恍惚的味道。当我能够理解一点并向患者描述时,她的目的就变得更加清晰了——实现一种“假死”,即以一种什么都不应该发生的方式来控制咨询。当她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这种控制时,她常常感到得意洋洋。

这方面的工作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虽然她害怕困惑,但这是她经常经历的。俄狄浦斯式的材料和感受一出现,她就感到非常困惑,害怕失去她已经得到的那一点理解。这立刻把她逼到了我刚才描述的瘫痪的控制状态,这样通常会使她平静下来。
等到咨询开始,我将展示她已经对自己的控制行为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那就是她的“分析性贪食症”(我们开始的时候她的贪食症还没有表现出来)。我的睡意几乎消失了,只在作为对患者特定防御姿态的一种特殊反应时会重新出现。
在我将要呈现的那次咨询之前,她对她从家人那里得到的一些消息感到非常沮丧和激动。就在那次会议之前,她接到了她姐姐的一个电话,她妹妹告诉她,她们的兄弟比尔(比尔是紧接在她前面的兄弟,住在她们的原籍)由于一些商业上的不正当行为而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她被这个消息弄得心烦意乱,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哆嗦。她反复提到,她的父母一直要求每个人都要诚实;她记得,当她撒谎时,他们曾骂她,但她补充说:“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银行有账户,大概是为了避税。”她还表示担心用她所谓的“被污染的钱”支付分析费用,因为她的个人的钱是从她的家庭来的。

星期一,她开始说她认为自己得了感冒,但她不想告诉我,因为我会说些可能不对的话。星期六的时候她止不住地发抖,但她以某种方式勉强能够应付。汤姆(她的长兄)给她打了电话,让她感觉非常糟糕。接着,她又急促而糊涂地叙述了她和汤姆从意大利打来的电话交谈。他们讨论了一个可能会有的全家聚会,因为他们的母亲想告诉他们一些她已做好的最后决定,这个决定将影响他们所有人,汤姆非常希望这个聚会在他在意大利的房子里进行。她用这样的方式报告了和哥哥的对话,他们似乎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分歧,她形容他是在恐吓和欺负她且蔑视其他兄弟姐妹。他还想让她把她的孩子和他的儿子(在英国的寄宿生)送到意大利去半个月。她拒绝了。他生气了并坚持要求,所以她最后告诉他,她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的儿子很残忍而她的孩子还太小了。
他回过头来坚持在意大利举行家庭会议,而她说,这种距离不现实,建议提出一个对所有人更等距的点。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言语和情感的涌现而来的。似乎有很多角色,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观点,她传达了一种被分裂成许多部分的感觉。她继续告诉我那是多么的糟糕,最后她告诉我,她给其他兄弟姐妹打了电话。
她说话的时候,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绝对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身上(在她的联想中的汤姆),(2)我也感到自己变得困惑了,我的思维同时向不同的方向移动。我本想在这里插一句,但我没有机会说什么,因为她继续告诉我星期六她的丈夫已经结束了一次演讲旅行回来了,她可以告诉他比尔问题的全部经过。她再次带来了用肮脏的钱来支付分析费用的恐惧,并且似乎为此感到非常困扰。

在呈现我的解释之前,我将讨论我认为在咨询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刚到的时候, A太太看起来受到了迫害,并且裂成了很多部分;当她以一个令人困惑的方式说“我很困惑”时,她投射了一些部分到我身上。她感到被误解的客体所批评,不得不将其拒之门外:她曾说她不能告诉我自己得了感冒,因为我会错误地理解它。在周末,A太太感到被我拒绝,因为我离开了她(特别是身在家庭困境中);她觉得我很残忍和自私。我的印象是,她将这种经历与坏的(移情)客体—我分开,并试图通过将碎片散布到她的兄弟汤姆和他的儿子中来解放自己,而她自己的孩子则代表了被残酷地对待的她。这一举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她在周末被拒绝的感觉,但却让她感到自己被外界“捉弄”了,而不知道为什么。她似乎害怕受到侵犯。她哥哥明显自私的行为助长了对他的这种投射。
在她分析的早期A女士非常频繁地使用分裂机制,这往往导致分裂状态。她使用碎片化的手法主要是防御性的,因此她经常感到虚弱和平淡,抱怨记东西困难。此时,A太太已经对她的敌对和分裂机制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总体而言,她对我的感觉更加整合,并且在复杂的感觉里感到挣扎,这呈现着她与原初客体的样子。在我展示的咨询中,周末分开的痛苦以及她与家人的困难使她再次采取多重的分裂和投射,这使她感到耗竭,动摇和内疚。我似乎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一个可疑人物,不仅对离开她很不好,而且对她使用的方法(分裂和投射)持批评态度。她可能会觉得我只会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即分离引起的敌对情绪),而看不到她希望保护她对分析和对我的好的感觉。
我认为在回到大量使用多重分裂的过程中,她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有多矛盾,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对她非常痛苦。随着体验我为同时有好有坏的“被污染的客体”, 她复杂的感觉以及对我的某些感受的投射威胁着她。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她试图通过将不良情绪散布到家人身上来保护我,但是当这种方法不起作用时,她因和“坏我”一起而感到危险,并且她担心作为坏客体的我会误会她。
现在我将带来我的解释:我首先说,她似乎被很多问题和人侵入,无法思考。她立即几乎打断我地稍微平静地说,“这是非常真实的”,并更详细地谈到了她是如何在20岁时拒绝从父母那里拿钱(这是在分析中知道的)。现在她补充说,这表明她是对的:一切都变得肮脏起来。我的发言似乎使我立刻松了一口气。在我开口之前,她已经感觉到我被她的幻想所威胁,看到我愿意并且能够工作,她就放心了。
我继续我的解释,说她似乎对我很害怕,她觉得我不友好,不关心她并且准备对她进行错误判断。(这是基于我的理解,我的缺席使她痛苦,并且这种失落所产生的感觉刺激了她对我的坏情绪的投射,使她感觉我是不友善的,并准备去误判她。)我说的是当她经历了如此多的感觉和问题,她感到我在周末休假很自私。她可能感到狂怒、非常脆弱和孤独。我继续说,为了感受不到那些,她把自己分开,并把不同的部分放在不同的兄弟姐妹身上,当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这些的时候她就诉诸于采取一些疯狂的行为。
我的解释是基于我的想法,但我只是请我的患者注意我刚才提到的几点。我主要讲了两点:她对我的看法和她的防御。我的解释是:我(在移情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坏物体,以及她是如何感觉以及为创造这些做了什么。我描述了她用来防御这种情况的防御措施,以及她与家人一起活现的方式。在考虑“何处”的时候,我因为容纳着她的混杂感受而感觉很不好。这个解释是面向分析师的,因为问题似乎就在那里——她以那种特殊的方式体验到的就是我,部分是因为分离,部分因为她的投射。在语言化了这些之后,我直接转向了她自己的行动。我直接讲出我对她内心感受的假设。至于什么时候,只有当我上面说的那些因素(非常自私的客体和碎片)在我的脑海中汇集在一起时,才有可能澄清情况并做出解释(使我困惑以及周围有人非常自私的普遍感觉)。

回到咨询中:在我的干预之后她先是放松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是若有所思。过了几分钟,好像有什么反应似的,她说她也想去汤姆家,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起去,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太美了,走在乡间的红叶上……她的声音听起来甜(这不是她的特点)和挑衅。她似乎也在说,好像有人在阻止她或禁止她去。当她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和她一起工作的感觉正在消失,就好像她漂到美丽的意大利时把我抛在了后面。我注意到她似乎在进行某种奇特的挑衅,我提醒她说上一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情况并不乐观,她似乎觉得我不想让她走。对此,她的回答是以一种混合着挑衅和微笑的声音,进一步阐述了整个家庭在一起时的友善程度和喜好程度。
她的回答令人费解,我觉得我的解释还不对,很可能我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被污染的钱,以及她对我以前的解释做出反应的理想化,以前的解释对于将碎裂的她聚集在一起很有帮助。遵循这些想法,我告诉她,在周末,她感到自己被我抛弃了,感到我很冷血,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各个方面分散到兄弟姐妹中,但是当她现在感到被我理解时,她不仅感到我是好的,而且理想化了我。她与我一起创造了这张理想和睦的画卷,这使我们感到彼此很亲密,但是她感觉到我不想让她走。我认为分析工作所带来的缓解,使患者希望与我成为一体,为此而把我拿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她认同了一个理想化的我。我所说的是一种投射性的认同,在这种认同中,患者投射出她的占有欲很强的感觉,导致她感觉被困在我里面。我看到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是,她将我分解为一个她想要成为并拿过去的理想的客体,而另一个我却是空的、被抛弃和生气的。我认为我的后一个版本的解释包含并反映了她在周末不得不离开的感受。
在短暂的停顿和她的一些评论之后我补充说,这种对我和我们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她的不良情绪的蔓延造成了一种假象,显然是为了保护她,不让她知道她对我有多生气,因为她也觉得我理解她;她觉得对我产生矛盾的感觉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通过体验我为肮脏的来用迷惑的感觉恐吓她,像我曾被肮脏的钱污染了那样。

A女士首先说了“嗯……”,然后补充说“这是真的”,稍停片刻之后,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了她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这再次是关于打包的梦(A女士在她的整个分析过程中都会做着将她所有的物品散落在身边,她无法将它们打包在一起,有时不得不将它们抛在后面,有时还会被卡住的梦)。在这个梦中,她在某个地方,她所有的东西都散布在周围。她发现很难将它们收集起来以便将它们放在手提箱中,而且没有足够的时间赶上第一艘船。但是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不必赶上第一艘船,因为那之后不久又有另一艘船了,所以她设法收拾了东西。她说这话时听起来很满意。
我解释说,我们今天的工作和我之前的解释帮助她理解和处理她正在经历的事情,只有这样她才能记得那个梦。这个梦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她试图把自己从坏情绪中解脱出来,把它们分散在周围,这样她就不会觉得我很坏或是一个好坏兼有的人,也不会对我感到太生气。我说,我认为她还保留着一些与好的我的联系,但她感到被矛盾的感情所拉扯,使这种联系变得危险,以至于她需要我帮助她。
A 沉默不语,有些沉思。然后她说了一些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的话,几乎像是用另一种语言说的。她提到了她丈夫的“宝宝”,谈到当他在抽屉里玩他所有的玩具时,她感到多么困难。她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怨恨。起初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试图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她没有主动提供任何信息。然后,我仍然不知道她丈夫的所谓活动,我的思绪集中在这样一种印象上:我的解释被她听到并同意了,但这让她感到怨恨。(我想在此提醒注意以下事实:尽管她所说的内容非常不清楚,但它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使我能够理解所涉及的情绪——我将在这篇文章稍后的内容中再次谈到这一点。)

现在回到咨询中,我解释说,她觉得我理解她,也理解我最后的解释,但随后她感到强烈的不满,体验到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炫耀着我是多么优越,能够保持我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抽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游戏”,而且在周一回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她直接回答了说:“是”,转到告诉我有关她度过艰难的周末以及与孩子们一起工作的细节。在这次咨询结束时,她说她已经收回了周六丢失的信用卡。这相当容易。她给Safeway(超市)打了电话,他们为她保留了信用卡。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已经恢复了更好的关系,赢得了信任,并在安全的地方建立了关系。
解释的工作是基于分析师对他的患者间的交流,如在他们的关系中所表达的,关于关系本身。正如我之前所说,分析师理解患者材料的方式取决于根植于分析师心中的理论。我自己的思想植根于Klein的理论以及Klein学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一节咨询中评估患者的交流时,分析师是警觉的,并集中在与客体有关的情感、焦虑和防御上。为了理解患者的交流,分析师必须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的持续变化保持警惕,这种变化表现在他在会话中的全部行为(语言和非语言)上。这些变化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分析师在观察这些变化时,试图确保他所针对患者的方面是对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分析师不仅要对患者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保持警惕,还要对患者在分析师身上引起的情绪保持警惕。这就是反移情,它可以作为一种感觉器官来感知患者情感的某些方面,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患者要么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表达,要么是补充了更直接的话语。为了理解和使用反移情在评估患者的材料投射性认同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投射性认同是由 Klein 在 1946 年发现的,她当时的理解主要是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投射到感到认同的客体上,主要目的是控制客体。
这个概念不断发展和壮大,是因为Bion在心理生活的发展中提出了它的首要重要性。Bion描述了母亲对孩子投射物的接受和感知如何帮助或阻碍婴儿的成长。特别是由于Bion、Rosenfeld和Joseph强调在咨询中使用投射性认同作为患者交流的方式,分析师开发并完善了反移情的用法,以了解患者内部客体关系的移情和性质、主要的影响和焦虑,以及因此而为患者防御的各种方式。所有这些构成了分析解释的核心,即解释的内容。

我现在想从概念上看一下本文所用材料中给出的解释。我认为此时在分析中患者已经到达了抑郁位置,她在苦苦维护与我的良好关系时站在她母亲的立场上,尤其是当暴露在分离中时激发了敌意。对客体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令人不安的矛盾心理,使她感到困惑。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情况的影响,并在她的内在世界中与自己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对抗由分离引起的敌对情绪的冲击,她回归到更适合于偏执-分裂位置的防御,主要是分裂(有时分裂带有一种碎片化的性质),投射性认同,朝向她的内部和外部客体,即她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但这些防御措施只起了部分作用,感觉到客体受到了污染。她觉得我自私而充满敌意,因为我离开了她,也因为她对我的投射;但她也意识到另一种视角。当这些动力被解释时,她感觉更加整合,她的第一反应是一种“夸张”的解脱,也就是说,她把我理想化为她的客体,并通过拿过这个理想化的我来认同这个理想的客体。这导致她身处一个双重的困境,既有歪曲又有她感觉被吸在这个“粘乎乎”的客体上。
当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时,她觉得我们之间建立了更好的关系时,她就可以记住自己的梦。这个梦表明,她的客体与她的内在世界有一种相当好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够可靠和牢固。她感到分析的周末分离引起的反应威胁着她,她再次求助于分裂和碎片化。当她从周末回来时,她需要在分析中测试和探索她自己的客体,也就是我(涵容她的投射),以便能够更牢固地确定整合带来的收获。在移情过程中与我之间的这种更好的关系不仅带来了满足感和积极的感受,也激发了她对我的嫉妒和对抗,这体现了她的原初客体。她体验我为一个能够理解她、同时又能轻松运用自己的头脑的人。她似乎体验到这对我就像是一场“游戏”。理解并向患者解释她的嫉妒以及她对我的感觉,因为这一切使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感受,这反过来又使她能够以一种更安全、更可靠的方式与自己的客体建立积极的关系。换句话说,积极的移情以更真实和坚定的方式占主导地位。
理解偏执分裂位置和抑郁位置之间的分析过程中发生的运动,使分析师可以评估患者在该时段的任何给定时间的水平。患者主要以偏执分裂模式工作将过度诉诸于投射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客体(咨询中的分析师)将被视为具有患者移入他体内的感觉,并会感觉分析师的行为以表达这些感受的方式对待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他自己的感觉的投射,那么患者的问题就在于他对分析师的看法。然后解释应以分析师为中心(Steiner,1993)。在已呈现的材料中,尤其是当我开始解释她觉得我很自私和反对她时,以及后来再解释我对自己的自我满足时(分析对我来说是一场游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解释的位置(何处)暂时放置在分析师身上。
在咨询的某个时刻或分析的特定时期,当患者能够通过涵容自己的冲突问题而具有更整合的功能时;也就是说,当患者以抑郁位模式工作时,解释的方向可以指向患者。分析师在这样的时刻判断患者在“何处”。通过变得更加整合,患者能够识别感受并对自己的感受负责。这可以从我呈现的咨询中给出的大多数解释里看出。我认为也可以看出,解释常常以一种快速的震荡方式指向感觉所占据位置的两方面(对分析师的看法和对自己的感觉的觉察),例如在“你感觉到我这样或以某种方式…因为你内在这样或那样“。当投射不过度且可能进行内摄时,解释性工作会帮助患者找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并进一步整合。

现在让我转向解释的“何时”。从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我谈论“何时”时,我指的是解释的想法在被患者接受之前在分析师的脑海中汇合的时间。
通过以开放的心态聆听患者与分析师进行交流的各种方式,最终会发生某些事情,从而导致分析师的思想形成一种模式,该模式为许多信息元素带来了情感上的意义。正是当这种情感发现和构建发生时,分析师才能够有位置构想出解释性假设然后告诉患者。继Poincaré在数学上的工作之后,这一活动被Bion称为“被选定的事实”。这是材料的要素,它将要表达的不同方面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一种新的构想。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分析师对患者进行了很好的调整时,正确的元素就会影响到他的思想并进行适当的整合,这种整合与分析师所感知的患者动力相对应。我认为这可以在当患者谈到丈夫“玩他的玩具”的材料中清晰地看到。尽管我不知道她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澄清她对于我和她一起工作的反应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使我能够像我提及的那样进行解释,然后患者可以朝向更深的内省前进。有趣的是,在她丈夫的“宝贝们——他在抽屉里的玩具”的表达中,很容易就可以推测出潜意识幻象的含义,这在智力上似乎是正确的,但这不是我内心里所意识到的东西。我心里想的是用一种刻薄的话语表达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反应。这是被选择的事实,当我解释它时,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分析师所构想的被选择的事实并不总是正确的。有时,这可能与分析师的个人反应或兴趣相对应,更多地是根据他自己的动力而不是评估患者的材料。Britton&Steiner用“被高估的想法”,来代替被选择的事实(Britton&Steiner,1994)。在他们所描述的例子中,最初被分析师高估了的这种被高估了的想法由于患者自身的原因而被束之高阁。我经常观察到,某些患者在遭受痛苦的不理解状态时,会不论是否正确都要尝试抓住任何事物,试图为这些令人恐惧和痛苦的状态提供一些光明。有许多情况所选择的事实可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把错误的元素聚集在一起,对应于分析师头脑中的一些干扰——他使用反移情的问题,分析师的任务是注意到它并纠正它。在我所用的临床例子中,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问她对在这样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举行家庭聚会的看法。我意识到某种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她对我的理想化。但是我太被她的话中的“甜蜜”和抗议的语气牵动了,从她的感受中传出我在阻止她去。我现在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我脑海中聚集的是对甜蜜的厌恶,这可能一开始使我无法理解甜蜜的理想化客体是我自己。

当一个被选择的事实正确时,通常会给分析师带来发现和清晰感(即使不是所有事情都被理解)。我也相信,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患者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似乎更有可能给他一个解释。(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患者会准备接受它,因为他的反应将主要取决于被搅动的焦虑,但他会以某种方式受到解释的影响。)本质上,我要说的是,“何时”分析师对自己的患者的材料有了新的理解,继而将咨询此时此地的各个方面集合在一起。
在本文中,我已经谈到了进行解释时分析师头脑中汇集的主要元素。对于“什么”我主要描述了的患者交流中的动力性内容;就是说,他的内在客体的那些方面与内在的焦虑和防御的关系,如移情中所表达的那样。在进行这些方面的解释时,分析师知道第四个“ W”;即“ 为何”。在理解材料时,“为何”指的是患者变成他这样子的原因,考虑到理解患者驱动力的作用与环境作用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理解“何时”中,分析师持续评估患者的反应——显示着患者的功能水平,如由偏执-分裂位置和投射或内摄进程占主导之间的波动所显示的;他以这种方式定义了“何处”。
当分析师通过整体交流中的特定因素将“什么”和“何处”联系起来时,分析师就到达了“何时”;
在那一刻,解释就可以在他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了。
References
Britton,R.& Steiner,J.Interpretation: selected fact or overvalued idea?Int.J. Psychoanal.,75:1069-1079.→]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 Vol. 3,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London:Hogarth Press,1975,pp. 1-24.[→]
Steiner, J.(1993). Psychic Retreats.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