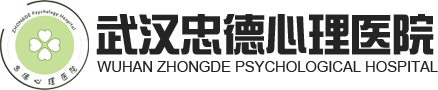与青少年的治疗联盟
Pasquale De Blasi, J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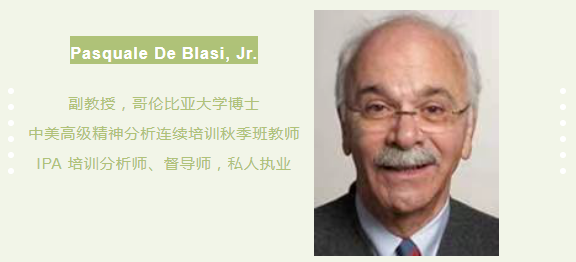
治疗联盟的概念
多年来,精神分析学家已经描述了需要发展和利用一个与病人的个性部分合作的意识,就像观察出现在分析期间的移情感受风暴里的盟友。在弗洛伊德1912年的论文“移情的动力学”中指出,矛盾的是,移情既是将患者与治疗联系起来并鼓励合作的压力,也是对分析的主要阻力。Balint(1952)将凝聚力称为移情的“成人的充满情感但是又会抑制目标实现的移情模式”。Bibring于1936年在精神分析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治疗联盟”的文章。Fenichel在1941年写到了“合理的移情”。Greenson(1967)在他写分析技巧的书中强调了这种与治疗师关系的重要性,他更倾向于称之为“工作联盟”。
所有这些概念都指的是分析师与对病人自我的观察部分之间达成协议的必要性,旨在对患者的内在经验进行诚实和不加批判的检查。
近来,为了更好的进行动力性的心理治疗,类似的联盟必须建立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心理治疗师将自己与患者自我中更健康、更现实导向的方面结盟,目的是观察适应不良,神经症性的防御和人格中冲突的部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联盟是由对朝向治疗师的感情和防御行为的正确的诠释而产生的。事实上,弗里德曼(Friedman,1969)在一篇优秀的评论文章中提出,治疗纽带的这一方面是治疗进展的结果,而不能引起治疗改变。当然,与青少年患者保持治疗联盟的结果是加强观察自我“没有自我判断评价和行动的内省力”(Long,1968)。

真正的自我观察是否会站出来
加强自我理想
Blos(1963)描述了青少年使用特殊友谊来加速自我理想的发展,Long(1968年)放大了它。这个特殊的依恋是和同性别的通常有些年长的朋友建立的。“关键的是,年龄较大(或体型较大)的人表现出一些年轻的青少年认为自己缺乏的必要的特征”(Long,1968)。然后,这些特征被理想化,以提供自己缺失的完美让自恋平衡能部分修复。这种关系后来被内化为一种稳定、但也是宽泛的内射。朋友的价值观逐渐被提炼并与他们的起源分离,并在青少年心中完全独立存在。再次引用Long,“因为这个男孩现在可以更好地接受他的本能驱动,控制并引导它们,他现在可以把自己更当男人看待,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更客观地对待自己,并最终更客观地看待他的父母。也就是说,自我理想的建立是自我观察发展的支柱”。
在与青少年患者建立治疗联盟的过程中,治疗师可能会发现他已成为上述意义上的年轻人的“特殊朋友”(参见Adatto,1966)。即使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治疗师允许去探索发现和维系这种与年长朋友的关系也可能是治疗中最重要的收益之一。当出现不带评判的自我观察能力时,许多青少年患者似乎以相对迅速的方式出现实质上的“自我治愈”。

促进治疗联盟
建立治疗联盟的基本技巧是如上所述的对当下的情感和防御及时解释。这个过程可以重申为帮助青少年识别到他的行为是由内在的感受状态激发的。在治疗情境的早期,这些感受状态通常是急躁、沮丧、无助的感觉,以及对自己有向治疗师咨询的需要而感到的自恋损伤。对抗这些痛苦感受的一些典型的早期防御包括反叛;被动顺从、胆怯;对治疗师的态度轻蔑、居高临下;冷静、超理智。认识到这些防御和他们掩饰的感受状态是心理治疗的第一件事。当青少年的主要防御是被动顺从时,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这些青少年表现为“好”病人,急于与他们的问题开始工作。治疗师不应该被欺骗,将这种被吓到的谄媚奉承与真正的治疗联盟混为一谈。

对自我的方式说不
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和见诸行动必须受到治疗师的限制。指导行为前行的唯一合理依据来自治疗师对有效治疗所需条件的了解。简而言之,青少年被告知他做什么行为不关治疗师的事,除非他做了一些干扰治疗过程的行动,这些行为是必须控制的否则治疗就不能很好的进行。通常情况下,也可以证明,见诸行动可以破坏年轻人的心理和谐,或者有可能会伤害他。治疗师试图传达他希望青少年能够在发展阶段的战役中获胜的愿望,然而要清楚的是这是年轻人的战斗,治疗师不能替他出战。无论这些症状是否“错误”,当治疗师明显的对所有症状行为都表现出同样的仁慈且具有探究态度时,这样的立场对于青少年来说才会更有说服力。
Sarah是一名15岁的女孩,由于滥交和学习成绩不佳而进行心理治疗,曾公开对治疗师的主张表示怀疑,认为治疗师对她滥交行为的反对不仅是基于道德愤慨。她嘲笑治疗师认定的——认为她的行为背后有她没有理解的原因的主张,因为这个不能解释她“性欲过度”的主诉。她继续相信这位治疗师曾在“另一个广场”,“有性烦恼的”,她试图以典型清教徒的方式干扰她的乐趣。
在发展了一些积极的移情后,女孩开始暗自研究。最后,她在一次治疗中带来了一张优秀的成绩单,这对治疗师来说无疑是一份诱人的礼物,也是对她的价值的证明。她起初感到生气,然后惊讶于治疗师没有赞美她的“好”行为。相反,治疗师注意到她似乎并没有享受这些成绩,这表明她努力学习是因为她觉得这些是她被期望的结果。她谈了一下她提高学业表现的动机,然后说:“你知道,我一直在告诉你我是一位性方面的行家。实际上,我愿意来见你的唯一原因是我从未享受过性爱。不止一次。我喜欢有关性的想法,但在实践起来是很糟糕的。但是我不断地实践、练习。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

治疗师也觉得这的确是很令人费解的情况,他提议和病人一起尝试去理解。
青少年对任何操纵控制都非常敏感,因为这种控制威胁着他脆弱的自主意识。除非治疗师对所有青少年的行为保持中立,同情但有探究的态度,否则他无法使青少年相信他的目标是促进理解,而不是通过心理战来支配患者。
“别伤到自己”
治疗师应该迅速指出青少年中倾向于判断和自我批判的态度。应该鼓励青少年去寻找他的行为、态度和情感状态的来源,而不是给他们贴标签。治疗的目的是增加自我理解和内在心理力量和灵活性,而不是抑制恼人的行为。通常,通过治疗室里与患者的互动,可以有效地表明治疗中立性和行为的动机来源。
一名16岁的男孩在椅子上懒散地点燃一支香烟,开始了他的前三次治疗。治疗师对这种行为含义的询问使他生气。
“你的意思是我甚至不能在这个糟糕的办公室吸烟?”
“我没有说有反对吸烟的规则。我只是注意到你从不谈论吸烟,但是当你击打椅子时你会点燃香烟。”
“所以呢?”
“所以在这里了解你为什么做你做的事情。”
“因为我想,好吗?”
“好吧,如果你想经历一个倒立着演奏口琴的治疗,我想这没关系,但我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男孩笑了笑,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你准备要告诉我父母我在这里抽烟吗?”
男孩垂下头。“是的。我知道我不应该吸烟。如果我父母知道的话他们会生不如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很坏。”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为了帮助你批评自己的。让我们试着去了解这里真正发生了什么。”
“然而,我很想看看你对吸烟的看法。”

吸烟行为表现的是他企图通过连累治疗师成为禁止行为的帮凶来腐败治疗师。如果不坚持揭露吸烟背后的原因的努力,治疗师可能会被操纵到一个妥协的位置或被迫发布独断的禁令。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会形成治疗联盟。然而,当治疗师能够平静地面对那个男孩操纵人的倾向时,男孩说,“是的,我喜欢按我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我猜”。
治疗师没有理会措辞中的性暗示,但解释说:“我确定你没办法足够信任别人到坦诚相待是有许多理由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试着理解的事情之一。”
最后,这个男孩能够轻易地谈论他所谓的“骗子倾向”,无论是对他的不利还是他们在情境中出现。他最终实现了在行动和感受中观察自己的能力。
走向真正的自由
上面讨论的年轻人终于能够意识到“正好在想”表现的特定行为实际上是他自己内部许多压力导致的最终结果。这种识别对于青少年的治疗非常重要。选择的自由正在被未知的内在力量的破坏,这一令人惊讶的领悟极大地增强了青少年的治疗动机。这个年轻人对自由和自治的愿望将成为对治疗师的支持,以便将反叛变为真正的自由和自我导向,而不仅仅是用盲目的服从来代替早年服从父母的本能驱力。

青少年内部的一些心理压力干扰了他接受这种正在解放的洞察力。青春期的典型自恋、无所不能的防御性结构正受到无意识动机的强烈威胁,并且通过对正式行动的关注和无所不能想法而得以强化。青少年感到迫切的想要将自己视为他命运的绝对主人。他不能无限塑造,但必须适应自己的本能驱力、自己的良心和外部社会需求的想法是有攻击性的且可怕的。完全控制的另一面是完全无助(虚弱)。当他的无所不能的泡沫被刺破时,青少年往往感到完全脆弱和可怜的虚弱。治疗师必须非常支持,有时甚至需要非常有力地说服青少年忽视地下室的火灾或只是试图“认为它走了”是一种让自己烧伤的绝妙方法。治疗支持包括帮助青少年看到他设计灭火方法或将火限制在安全区域的真实能力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简而言之,治疗师支持青少年的自我技能来阻止他对神奇的全能感的信赖。
在处理同样的技术问题时,Holmes(1964)提出了一种有趣的技巧,即在短时间内让叛逆的青少年扮演合作且友善的角色。他觉得这种装置经常调动贯注于在自我融洽的症状行为中被吸收的情感。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已经描述了一些处理在游戏中作弊的潜伏期年龄儿童中类似问题的技巧。许多技术方法也适用于青少年(Meeks,1970)。

青少年对待治疗联盟的态度
罪恶的联盟
本我联盟和摆荡的治疗师
所有罪恶的联盟对青少年病人都是危险的。本我联盟特别诱人,因为治疗师往往渴望比青少年批评的其他成年人更能理解,宽容和“时髦”。发现自己在讨论性行为的具体情况、瞒骗父母的技巧或治疗早期的官方权威的胡说八道的治疗师,可能会怀疑他已被吸引到与本我或本我组织的罪恶联盟里了。这种联盟的结果是削弱青少年的管控功能和增强他们浮躁的见诸行动。缺乏真正的联盟可以通过很快会指向治疗师的明显的敌意表现出来,可能是因为青少年无意识地在邀请外部的控制。至关重要的是避免与青少年这样结盟,因为他的自控力很差,而且他对自己强烈的感情和冲动感到混合的恐惧。由于担心失去控制,许多青少年会对本我联盟产生强烈焦虑的导致防御,作出沉默和试图回避整个治疗进程的反应。治疗师被视为一种真正的威胁,一种鼓励他们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并放任其本性最糟糕部分的诱惑者。


与病理性自我防御的联盟
在青少年的邪恶联盟中可能使用的主要的病理性自我防御是理智化。聪明、心理敏感的青少年,通常对流行心理学(甚至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弗洛姆等)非常了解,可以讨论几个小时的迷人见解,同时保持完全不触及治疗。防御甚至被积极地用于在伪装的热情合作下活现对治疗师的竞争和贬低态度。如果治疗师图安逸不与那些不合作的、带着病理性的防御加入联盟的青少年交战,治疗联盟就不会出现。相反,治疗将恶化成贫瘠的哲学讨论,逐渐在治疗师和患者中产生厌倦和绝望的感觉。
在青少年的治疗中,这是一个可以进行思想性的讨论的地方,甚至可以讨论理智化的防御。然而,重要的是首先要建立强大到允许进行情感体验和报告情感经历的治疗联盟。这只能通过在与青少年建立情感联系之前,避免在治疗早期广泛讨论概念内容来实现。应该要求理智化的患者定义所有术语,如“敌意”,“矛盾”,“色情”,“乱伦”,“真正有意义”,“我-你们的关系”等等。他被问到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并被要求在涉及真实生活互动时将这些具体的词与具体经历和感受联系起来。当然,治疗师避免使用任何技术术语来代替满载情绪的日常用语,如“疯狂”,“生气”,“烧伤”,“性”,如果这些词对于特定患者来说似乎并不诱人甚至可以用俚语短语。不鼓励概括而要寻求具体细节。当然,目标是将真实的情绪带入咨询。当情感确实出现时,无论是描述心理治疗之外的事件还是直接与治疗师的关系,都会受到治疗师表现出的兴趣和接纳的鼓励。

一名18岁的大学新生因为在服用LSD(致幻剂)后变得像精神病一样,进行了精神病评估。即使在短暂的明显精神病消失后,他仍然相当浮夸,专注于善恶的宇宙问题。尽管人格结构脆弱,但限定目标的心理治疗似乎是可行的。
最初,虽然没有受到鼓励,但一般的哲学结构和先占观念被接受了。治疗师在观察中偶尔插入这样的想法:重要的个人感受似乎在病人的想法中缺席了。患者打算克服自己感受的反对意见受到了友善的怀疑。这位极其聪明的年轻人被哲学系统创新者的性格怪癖所扭曲历史的例子提醒。与此同时,病人不经常提到的自己的“人性弱点”被称赞为他渴望了解自己的证据,从而避免了其他思想家的盲目错误。渐渐地,尽管治疗师不得不继续拒绝病人试图让他扮演智者的投射,但病人已经具备了自我观察的能力。
人们没有克服自己感情的信念被不断重申,并且治疗师尽可能地向病人展示自己的行为。治疗师一直坚信,他唯一的能力权限就是理解情绪,这种技能是特殊训练的结果,而不是任何超自然力量或神秘天赋。渐渐地,患者能够承认他的冷漠、神秘的优越感大部分都包含了焦虑和自卑感,哲学上的超脱常常是他处理沮丧和无助感的方式。
在接近被表现的热情的和平主义和其他面向的自虐转向掩盖起来强烈的愤怒时,需要更加谨慎。只有在多次向他证明治疗师有能力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而不对他采取行动之后,才有可能直接评论他的愤怒。他对自己的侵略性冲动失控的恐惧强度可以通过他感觉到的“邪恶阴谋”的妄想投射来说明,这是在他最初的精神病发作期间感到试图让他“杀人般疯狂的”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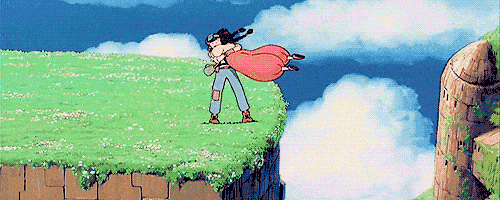
与超我的邪恶联盟
在青少年心理治疗中,几乎不可能完全地避免与超我形成邪恶联盟。青少年能很自然地练习将他的良心外化。这种发展上的特征将被带入青少年与他的治疗师的关系,因为它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与所有重要成年人的互动中。这种倾向通常表现为诱使重要成年人采取虐待性惩罚的煽动策略。第一章的部分详细描述了这种模式,该部分讨论了青少年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治疗师作为一个重要的环境性人物,必须时刻警惕与青少年患者建立这种关系的危险。为了限制防御见诸行动的技术上难免会要求治疗师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从中很容易滑到一个与超我的联盟里。

一个13岁男孩的随和可爱被成功解释为对他内心感受的抵抗。这个男孩的父亲是一个愤怒、苛刻、有竞争力的男人,每当他父亲的规则或说法受到挑战时,他就会袭击这个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能够在一次会议中讨论他的一些愤怒,在此期间他能够认识到他过分尊重和通过服从来躲开治疗师是他与父亲一起用来掩盖他内心愤怒情绪的一种防御性模式的延续。
然而,在下一次会议中,他沉默且忧郁。在咨询即将结束时,他突然说他“走了”并且径直走向门口。
治疗师相当惊讶,试图让他留在房间里,并开展了一场温和的推搡比赛。治疗师认识到他的错误并且在下一次咨询中没有遇到一个非常消极的年轻人感到惊讶。他讨论了男孩“挑起战斗”的需要,并表示他有兴趣了解这个男孩留在办公室的感受。治疗师祝贺这位年轻人在咨访关系中表现出更加诚实的表现,年轻人也确信他的愤怒是可以被讨论的。
当然,青少年确实需要将超我问题外化,以便找到修改其严苛的道德的方法,同时使用外部媒介作为对表达不明智的冲动的临时保护。青少年治疗师可以期待以被这样使用,并且可能通过容忍他的扭曲的意图而有所帮助。一个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例子,就是在困难时期继续治疗的问题。在许多青少年的治疗期间,以下对话的某些版本是周期性的常见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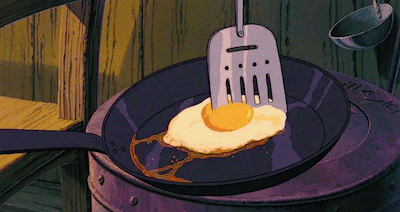
青少年(愤怒):我从来没有必要来这里。我绝对不需要你,而且我不会再回到这里讨论这些愚蠢的谈话了。
治疗师:这并不太令人惊讶。我们都知道,当事情让你太紧张时,你会有逃避的倾向,但你有足够的力量留下来谈论你的感受。
青少年:我为什么耐着性子听这?我必须回来吗?
治疗师:你知道你需要治疗。那不是问题。你真正想通过这些退出谈话做什么?
青少年:好的,好的,下周我会在这里。我本应该知道你不会让我退出。
治疗师:为什么我不要阻止你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
青少年:噢,忘了吧。我不会放弃你的珍贵的治疗了。
治疗师:对不起,我不能忘记它。只是不退出并不会停止。我们需要去看看你是如何构建我的。
青少年:上帝!即使是我的父母也不是这么难相处的。
治疗师:也许他们主要对你的行为感兴趣——你做了什么。我感兴趣的是你做事的原因和感受。有时候去做认为我希望你做的事情比观察你的感受要简单得多。无论你是否戒烟,我的任何业务的唯一原因是它会干扰你的治疗。你是否退出,和我有关的唯一原因是它会干扰你的治疗。
青少年:非常好笑!但你确实说我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
治疗师(笑):是的。 Simon Legree(奴隶主)再次骑马。
青少年:啊哈!你承认了!
随之而来的是青少年迫使治疗师进入超我的角色。尽管如此,治疗师仍然必须抵制住他对治疗师的挑衅、威胁或以其他引起惩罚的行为引发治疗师批评他们的诱惑。这并不意味着治疗师就避免了超我问题。之后,我们考虑在这个领域以一种鼓励情感成长的方式处理这些素材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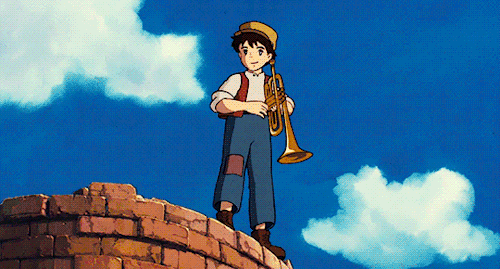
当前的观点是,只有观察的自我才是青少年治疗中可靠的盟友。即使超我联盟导致外化的行为减少,也不会获得真正的成熟。在大多数情况下,表面改善趋于短暂。在其他情况下,它通过一种禁欲的人格收缩来维持,这种限制扼杀了自发性和快乐的能力——为肤浅的社会化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控制都没有任何好处。
识别联盟
如果治疗师能够避免形成邪恶联盟,并以适当的同理心,机智和精确的方式回应青少年的防御行动,那么治疗联盟的证据就会开始出现。重要的是要识别并认可青少年这一重要的新技能,而不是家长式地认可“好”行为那样暗示。或许,对联盟最有意义的赞同是仅仅认可其在治疗过程中的价值的评论。它的价值纯粹是“工具”,它是一种保证治疗工作更有效的工具。
然而,为了信任青少年的发现,有必要认识到它的表现。根据青少年患者的风格和个性,联盟可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人们主要通过咨询中语气的微妙变化来识别它的存在。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完全是针锋相对的。治疗师直观地意识到他可以稍微放松下来,因为他的病人至少有兴趣观察和理解在早期的治疗中表现出来的惊恐、警惕、戒备和迂回的风格。简而言之,治疗师不再感到他是独自在反对患者的阻抗了。

联盟的检查点
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一般“感受”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细节来检查,这些行为细节通常证实了联盟的发展。
1)患者偶尔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者“我想我明白为什么会这么难过”,或者“你能理解我真正感到沮丧的是什么吗?”换句话说,患者表现出恢复他的情感体验的倾向,或者至少是愿意让治疗师说明高张力感受状态下的潜在动机。如果所讨论中的情感体验直接涉及治疗师,这尤其有意义。“我认为你的评论让我如此生气的原因是……”
2)从威胁行为转到讨论思考并探索其起源。取代“我不会回来”的是“当你说出我对你这么生气的事情时,我想退出”。
3)矛盾的是,治疗联盟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对丧失冲动控制事件更宽容的态度来表明。这些事件是以温和和客观的方式进行讨论的,而不是在自我厌恶的背景下被隐瞒、吹嘘或批评。然而,不仅仅是理智化的态度,因为伴随的情感不是被孤立的,而是可以被讨论的。青少年可以说,“我输了一场战役,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我赢了整个战争”。
4)对治疗期间出现的影响的认可和讨论。患者能够描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次讨论让我非常紧张”。
5)承认并接受矛盾心理作为内在现实。不再是“我的父母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我”,而是“有时候我想长大,但有时候我很害怕死亡”。
6)对恰当的对峙和解释展现出反思、好奇的反应,而不是防御性的批判性的反应。
在治疗联盟的信号到来前所有这些态度都可能表现为孤立的事件。它们仅代表一些可以作为验证上述一般合作氛围的检查点的特定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整体意义上的治疗师没有被患者接受为合伙人,这些行为就毫无意义。

维持联盟
治疗联盟是一种易碎的结构,不断受到其运作产生的焦虑的威胁。联盟的成功运作反复导致对工作联盟构成威胁的侵略和性欲化的高涨,特别是因为这些感觉经常直接朝向治疗师。青少年不断寻找真实物体,很难理解移情的意义和本质。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青少年心理治疗中移情的整体管理。在此环境中仅提到它是一种表现为对抗治疗联盟保持的主要压力。
在青春期期间描绘自我功能的波动特征本身就是对治疗联盟的稳定维持的威胁。在显著退行期间,合理的治疗联盟可能会与其他面向现实的自我功能一起被破坏。青少年治疗师必须具有灵活性,并使自己适应青少年从一个疗程到下一个疗程所显示的功能水平和防御模式的惊人变化。青少年患者自己通常不会将这些“情绪”视为自体的可变投射。他倾向于将每个新的自我状态视为他“真正”去感受的方式以及“真实”生活的方式。治疗师必须尝试利用治疗联盟来帮助患者接受他的复杂和变多变。Westman(1970) 建议当青少年似乎问“我是谁”时,治疗师往往最有帮助回答:“很多人。这取决于你内在的环境和周围的环境。“治疗师帮助青少年保持一种”完整性“和个人的连续性,尽管情绪和态度的变化快速且令人费解。
对联盟的外部威胁
除了内部危险之外,联盟也可能受到外部事件的威胁。父母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或有意识地因为各种动机破坏联盟。占有欲强的父母可能会受到治疗师和孩子之间的充满情感的关系的威胁。控制、敌对的父母可能将治疗师视为他们控制的代理人,并将这个形象传达给他们年轻的孩子。其他父母实际上可能会受到他们观察到的青少年进步的威胁,如果这些变化干扰了和家庭模式有关的很重要的神经病的稳定性。一些关于管理这些问题的想法在第6章中介绍了,对待青少年患者的父母(的问题)。

其他外部事件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青少年被迫建立一段时间内无法探索的僵硬防御。这些事件可能是青少年世界中重要人物的疾病或死亡,也可能是青少年在胜任和接纳方面的个人斗争中的压倒性失败或沮丧。在这些时期,青少年需要退缩和哀悼。治疗师必须认识到这种需要的合理性,并接受被动和移情的分享的角色,直到青少年准备再次工作。在这样的时期内更积极的干预可能长久地损害治疗关系。
这些实例确实允许治疗师观察青少年处理丧失的风格。他可以确定青少年是否通过完全内射客体来避免悲痛和哀悼,而不是逐渐认同所爱的人可取的特征,拒绝那些不符合他意愿和人格需求的特征(Laufer, 1966年; Root,1957:Rochlin,1965)。当哀悼过程出现扭曲或被青少年避开时,治疗师可采取行动以鼓励适当表达悲伤和有建设性的适应丧失。然而,当青少年的悲伤和哀悼是恰当的时候,治疗师应该保持低调,并为完成工作留出必要的时间。
在联盟形成之前要做什么 - 当联盟没有形成时
治疗联盟可能根本就不会实现。这可能是由于对特定患者的早期防御或情感未能准确或有效地回应。在这些治疗错误的例子中,对问题的公开讨论可能是允许重新开始的保证。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可以考虑将患者转介给其他治疗师。然而,在进行转介之前,治疗师有必要仔细检查他的决定,以确保他的计划不仅仅是基于反移情的对青少年的拒绝。即使证明是这种情况,转介仍可以是有序的。然而,如果转介的真正原因能被识别和讨论,治疗师和青少年都将受益。
当患者根本不适合门诊心理治疗的时,问题就有所不同了。无论诊断过程多么谨慎,都会出现一些错误。当这被认可时,必须向患者及其家人提出问题和新建议,而不得过度尴尬或道歉。有关结束的章节将进一步讨论这种情况。

为什么青少年为联盟而奋斗?
在调查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有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治疗联盟能够在它遇到的变迁中幸存下来。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些消极力量会受到两种积极影响的对立而达到平衡。第一个是自由和放松的感觉,这通常是自我意识的提高的结果。由于从治疗中获得了控制感,青少年有动力坚持不懈。青少年在与工作的治疗师的认同方面的愉悦支撑了这种合理的优势。青少年患者发展成为心理治疗师的野心的频率揭示了身份确认的和至少经常是被动地失去身份的防御性恐惧,除非他们变被动为主动的“还是治疗师的方式更好”。在我看来,这种防御不应该受到挑战。相反,青少年应该被允许将自己视为初级搭档和最终同伴,只要他不破坏性地使用的心理洞察力来对待自己或他人。毕竟,当治疗联盟运作正常时,青少年在很多时候都会照着他自己的治疗师的方式运作。即使青少年破坏性地使用他新发现的技能,也可以在不攻击身份认同的情况下解释这种做法的反常。
Sarah,这位早先描述了滥交的症状的15岁的女孩,有许多前俄期问题,这可以通过她妈妈列举的童年早期众多口欲化的行为来说明。
在治疗的中期,她在观察和解释她的行为和感受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专业知识。在此期间,她与母亲的关系交换了过来。母亲看到病人(sarah)的小猫已经非常大了,照顾着母猫。她愤怒和厌恶地反应说,这么大的小猫“不会让他们的母亲独自一人”。莎拉解释她的母亲不赞成性欲的愉悦,并与母亲对性行为的负面陈述联系起来。然后她告诉治疗师她指责她的母亲因为神经质的克己而长期不开心(顺便说一下,这是正确的解释)。她告诉母亲她真的应该看一位精神科医生。母亲非常愤怒并谴责莎拉因为缺乏“真正的基督教徒”而需要精神科帮助。

莎拉最初对她母亲的反应感到愤怒,“当我只是想帮助她时。”治疗师注意到他在莎拉的评论中无法察觉到应有的同情和理解。可能是因为莎拉对她母亲生气和批评,只是将她的洞察力作为一种更有效的攻击武器吗?
莎拉能够接受这种解释,并转而探讨她对母亲对猫态度过度反应的来源。她最终识别出了她对侵略性索取的猫的认同和她内疚的感受,因为她的母亲加入了她自己的愿望,却通过悲伤和牺牲的氛围诱发内疚。
后来在治疗中,她变得有同情心并对母亲产生了深情的理解。她能够支持和鼓励母亲找到社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母亲的依赖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不会感到羞耻或自我厌恶。
失败的联盟的证据
治疗联盟已经崩溃的认知通常来自对整个治疗情况的直观把握,这被认为是联盟存在的最佳证据。人们会感受到一种新的反对倾向,与其说反对是对治疗师,还不如说是抵制治疗工作。再一次,治疗师感觉到他独自在努力利用治疗帮助自我理解的过程中奋斗。青少年不再配置另一只桨,治疗师必须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逆流而上。
同样,有一些孤立的事件有助于确认整体印象。

联盟失败的检查点
1)没有任何自我观察和探索的证据。青少年再次沉浸在经历中,并且在理解他在创造个人情感体验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有效地应对这些经验上几乎都没有兴趣。
2)针对治疗师的微妙或显而易见的行为,即使被提到也因为觉得不重要而不予理会。例子可能包括迟到、缺席会议、打断治疗师、频繁误解治疗师的话语,以及其他敌意表现,还带来礼物,赞美治疗师和其他诱惑性的行为。
3)先前被解释、理解和放弃的防御态度再度出现。同样,这还伴随着对行为意义的漠视。
4)对治疗师的操纵行为和态度的退回。换句话说,退回到用行动来与治疗师进行神经质的人际互动,而不是诉诸于语言化的探索。
重新建立联盟
如果治疗师识别出治疗联盟的中断,他就可以努力修复它。治疗师应该认识到,在联盟重建之前,没有任何工作会有用。无论在治疗中出现的内容本身具是多么兴趣,治疗师应仅利用那部分可能有助于重建治疗联盟的材料。在没有工作联盟的情况下,治疗师的干预将无效或甚至是反治疗的。

那么治疗师怎样才能重建联盟呢?第一步是确定联盟瓦解的原因。如上所述,最常见的破裂根源是经由治疗联盟本身的活动释放的焦虑和不舒服的情绪反应。一个非常诚实的18岁女生,面对她的阻抗,简洁地说明了问题:“审视自己的烦恼的感觉很不好。”
当然,这是治疗的主要内容。治疗师应该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好好地进行心理治疗会产生疼痛,而所有人都会尽量避免疼痛。青少年患者完全有权抱怨,并期望得到治疗师的同情。人类总是在现实的痛苦的需求下苦苦挣扎。当青少年在这些刺草上烦恼时,我们可以同情和支持他们。当然,治疗师的同情心是帮助青少年承受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而不是为了屏蔽伤害。
当面对治疗联盟的中断时,治疗师需要巧妙地向患者告知他们关系的变化。通常情况下,治疗师必须向青少年解释这种变化不被视为“混日子”的固执己见或难以控制。如果青少年要学习如何客观地观察这种互动,而不感到被治疗师批评,那么抵抗治疗师和抵制治疗过程之间的区别通常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澄清。必须帮助青少年理解,他与治疗师的互动是和治疗师对其他情感体验以同样客观、好奇以及非评价性的方式对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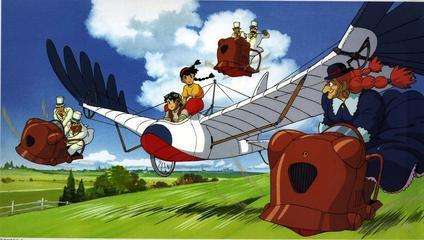
Tammy是一个有吸引力且身材娇小的17岁金发女郎,她在一天晚上因为学业成绩不佳的家庭争吵中而被要求进行心理治疗。她告诉她的治疗师,她希望接受治疗的真正原因是感觉她的生命正在流逝,而她无法形成有意义的亲密友谊。在最初的几次心理治疗会谈中,Tammy与治疗师建立了温暖的关系,并利用自己的内省能力,在理解她与勤奋、紧张且有点被动的妈妈的关系上有了一些成就。她能够认识到,糟糕的学业成绩同时反映了她拒绝像妈妈那样焦虑的生活方式以及她害怕与母亲竞争。
在这段时间里,她周期性地抱怨她似乎并不受欢迎。虽然她首先将这种不受欢迎归咎于她的道德标准,她认为这种标准高于她学校中大多数女孩的道德标准,但她逐渐认识到她在某种程度上“灭掉”了对她表现出最初兴趣的男孩。当治疗聚焦于这点时,治疗师解释说,Tammy似乎并没有认真对待她的女性特质这一事实,并且似乎在很多对待男女生之间的关系方面,就像在对待一个没有任何强烈感情的游戏。Tammy当时的反应是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治疗师的解释,并且防御性的声称她已经在拥吻了,并且她不再害怕性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采访中,Tammy显然很焦虑,发现很难谈话。她坐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时不时就拉她的裙子。她倾向于避开治疗师的直视,并且每当她试图说话时都会脸红。几分钟之后,她能够变得放松一点,但似乎在一个非常浅的层面上来谈,并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的感受、思想和行为具有个人特色的好奇。当治疗师解释说Tammy似乎对探索她的感受失去了很大的兴趣时,Tammy觉得她受到了批评。在治疗师澄清事实并非如此之后,并提议可以公开讨论关于治疗和治疗师的感受,Tammy能够说出当她离开之前的治疗并且意识到她非常沮丧。她进一步表示,她不记得前一节治疗讨论的主题,并主动说这对她来说很不寻常,因为通常很容易记住她的治疗。治疗师支持她在这件事上诚实的表达并鼓励她继续谈论她对治疗师的任何可能有的反应。

最初,她说话时有些胆怯,但随着Tammy开始抱怨治疗师是在“寻找问题”——她不知道自己有的问题时,这种情况逐渐减弱。正因为此,她不能确定治疗是帮助她还是让她更糟糕。她指出,一般来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心情愉快,但过去一周她一直比较沮丧。在这一点上,治疗师提醒她——他解释说她有时把生活视为一场游戏并拒绝认真对待,并且指明也许因为她试图去避免抑郁的倾向,所以她认为这样的游戏态度是必要的。治疗师支持她的诚实面对这些悲伤的感觉,并想知道从长远来看哪种做法最有保障。
“好吧,如果你能忍受一个哭泣的白痴,我想我可以通过它哭泣。我想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Tammy回答道。
似乎Tammy的不适与被治疗师直接识别出Tammy的女性特质所激活的对治疗师的性的感觉有关。然而,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治疗联盟来处理这种材料,恰当的反应是处理治疗过程中为了重建治疗联盟而产生的不舒服的影响。下一章将讨论青少年色情性移情的管理技巧。
如果联盟的中断是由青少年生活中的一些不幸事件引起的,那么在任何重建治疗联盟的尝试之前都需要一段不引人注目且不苛求支持的时期。如上所述,治疗师必须允许青少年主动表示有兴趣继续治疗的探索工作,除非悲伤反应本身被严重扭曲。更有可能的是,青少年通过抱怨“我们最近似乎没有在这里做什么!”来表示愿意回到工作。抱怨的青少年可能会非常惊讶地看着他在哀悼期间有点担心的治疗师,突然笑着说:“伙计,我不能告诉你,我听到你这么说是多么宽慰!让我们赶紧的吧。”

必须识别出联盟中父母的破坏,并区别于治疗本身产生的压力。通常,父母的干涉是通过否认以前与父母发生冲突的地方来示意的。相反,青少年向父母报告的“治疗疗程”,可能会暗示他们可以比治疗师帮助更多。特别是如果这些时期与父母的紧急电话重合或伴随,则有理由怀疑父母的破坏。这些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但很容易认识到一旦达到这个水平这个问题不能与青少年患者单方面地处理这些问题。父母本身必须通过一个协作的治疗师或直接通过家庭会谈得到帮助。
正确的联盟
治疗联盟不仅对任何心理治疗都至关重要;它恰逢青少年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观察自我的出现。因此,与青少年患者建立和维持治疗联盟具有双重重要性。我们已经探讨了在这个性心理发展阶段建立治疗联盟的一些特殊问题和陷阱。我们还试图指出,联盟的维持与治疗的其他各个方面密不可分,尤其是在青少年的移情倾向和青少年父母的问题的方面。建立治疗联盟的能力是青少年治疗师的基本技能。然而,如果没有能力在治疗过程中不断重建关系,这项技能就毫无用处。治疗联盟脆弱的结构是青少年心理治疗的核心支持,但如果没有持续和熟练地关注那些持续冲击联盟的势力,这种结构就无法建立。
我们现在转向考虑正在进行的治疗过程,包括讨论对联盟最普遍的威胁,那些对治疗师的非理性感受——通常用不完全准确的话称作移情。
引用和推荐的读物
Adatto, C.P. 1966. On the metamorphosis from adolescence into adulthood.J. Amer. Psychoanal Assoc. 14: 485-509.
Balint,M. 1952. Primary love and psycho-ana technique. London: Hogarth Press, Ltd.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Freud,S.1912. The dynamics of transference. Standard Edition, Vol.12,pp.121-144
Friedman,L. 1969.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Int J. Psychoanal. 50(2):139-153.
Greenson, R. 1967. The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Vol. 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Holmes,D. 1964. The adolescent in psychotherap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Keith, C.. 1968.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in child psychotherapy. J.Amer. Acad. Child Psychiat. 7: 31-43.
Laufer,M. 1966. Object loss and mourning during adolescence. Psycho- anal. Stud. Child 21: 269-293
Long,. 1968. The osberving ego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Rev. Inst. Nac. Neurol. (Mexico)/2: 8-21.
Meeks,J. 1970. Children who cheat at games. J/ Amer.Acad.Child Psychiat. 9: 157-171.
Rochlin,. 1965. Griefs and discontents: the forces of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Co.
Root,NN.1957. A neurosis in adolescence Psychoanal.Stud. Child12 : 320-334.
Westman, J. 1970. Personal communication.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