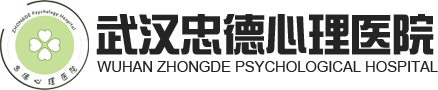清明祭扫,在哀伤告别中向前

文|何筱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作为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这一天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在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底蕴中,礼占据着一个不小的篇幅,清明的祭祖扫墓提供了一个连接家族同姓的机会,在文化上更多的被赋予守礼得仁、文化传承的角色功能。
记得年幼时跟随大人去祭扫祖墓,满山转悠,记住的是被大人安排在祭扫仪式即将结束时的作揖长拜,那时只是感觉到新鲜、热闹而已,那种新鲜是一种还被小家庭好好保护的年少幸福,心里没有半点悲伤,无从体会大人们认真给坟墓除草翻新、摆上祭品、放鞭炮时所有的感觉,即使被介绍某处墓穴埋葬的是何故人、与自己有何渊源关系,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等再长大一点,作为女性的我就被留在家里和家族的同性们一同准备男性祭扫完毕后的饭食,觉得好生无趣但又无可奈何。成人后某次在舅舅家,我被母亲、姨妈叫去到外公、外婆墓前看一看,来到墓前,简单地清扫后,姨妈开始向地下的二老描述生活的不顺意。那是我第一次在非清明节看到一位女性站在坟前去和逝者诉说,这单方对话的过程,是一种投入地倾诉,就好像两位老人真的在认真倾听此间的言语,而只是沉默以对罢了。作为旁观者,我被场上那种淡淡的氛围感染着,顿时又想起听过的那些故事——逝者托梦说墓穴如何不妥,而生者会认真按着托梦的指示去对墓穴做一些完善,不禁觉得,这个呼应本身好像是更多地满足了梦者的一种情感需求。

再后来,学习心理学,知道了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只是可能多数人并不经常用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的世间经历——出生时与母体子宫的分离,断奶时与母亲的分离,入学时与家庭的分离,步入婚姻时与原生家庭的分离,渐入中老年时与蓬勃生命力的分离。
当孩子遗失心爱的玩具时也许面对的是父母一句“我再给你买一个不就完了”,他们或许没看见孩子所失去的是一个特定的心爱之物,不是可以被随便替代的;当青少年步入大学离开家庭的时候,父母的失落被孩子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所替代,异地的电话联系中父母多用嘘寒问暖来填补可能没有共同生活经历的空白;当朋友们经历恋爱失败时,我们总爱以“天涯何处无芳草”、“塞翁之马,焉知非福”作为劝解常用句,甚至告诉他们结束一段关系的最好方法是开始下一段关系;当遭遇亲人离世时,我们需要在三天的丧亲假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们很少有机会为重要的丧失准备足够多的时间来完成告别,很多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中,悲伤和痛苦是被限定表达的——是一个需要快速摆脱的状态。而一个可以缓慢去消化的哀悼,似乎更显奢侈。无法慢下来的哀悼,和对脆弱的羞耻感有某种联系,表达哀伤和悲痛,容易被视为脆弱的、不适应的,对他人评价的在意,对自我脆弱的怀疑,让我们想要对那些或浓或淡的哀愁避而远之,不谈、不思、不忆。

其实,从适度的哀伤中我们才能更好的发展出告别和前行的能力。弗洛伊德在《哀伤与抑郁》里提到“在对失去的客体的每一个回忆和期待之中,现实带来评判,这个客体已经不存在了,此时的自我是否能接受这个命运呢?在自恋性的满足下,为了生存,要解除与失去的客体的联系。可以设想,这种解除过程是非常慢且一步步的,在这个过程结束时,对于其必要的付出也没有了”。适度哀伤是一种适应,也是一种向前发展所需的必经过程。对哀悼的禁止和压抑很有可能是拧紧了一根本来就已经绷着的弦,指不定哪天,一个偶然的、并不强大的刺激也可能让个体感到崩溃,正是一根稻草也压死骆驼。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但时间并不会自动生效,能让时间生效的是人们愿意把那些藏于心中的浓厚情绪在时间的尺度上去摊开,去沉淀,去升华……
丧失,是关系的终结。但一段关系的终结并不必然改写个体所有社会关系,一个健康的人可以通过适度的哀悼,将自己的力比多能量从不复存在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上,也可以通过内化这个个体好的特质,以此来完成一种精神的继承,让个体的生命厚度和色彩得到丰富和立体化。

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像古人一样遵守父母亡守孝三年的制度,清明祭扫成为文化中被保留下来的一种形式,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站在彼处,回望起曾经深深存在于我们生活经历的人,哪怕面对的只是冰冷的墓碑,情感还是能从记忆的深海里涌出来,尽管这种表达也许更多的是内心的言语,并不付诸于口头的声音。这是一个仪式,却又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每一次的回头与重温,是内心不断地拿起与放下——从混乱到清晰,从重负到熟稔,让我们的生命之源继续奔向前方的大江大河。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