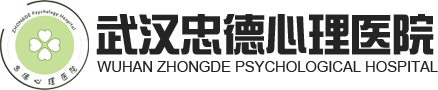本文系Alice Feller于2009年所写的文章,题目为《Termination》(治疗终止),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7(5):1185-1195.
每一次分析都是为了结束而开始的。
分析师把这种结局想象成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师和来访者对结局达成一致,花时间探讨分析的收获和失望,探讨结束的问题,特别是分析组合的分离。
然而,在实践中,终止对精神分析师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Mary Margaret McClure在小组讨论开始时概述了这种两难境地。她说,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对终止协议的关注存在滞后。这种滞后似乎反映了对精神分析的目标、有效性和分析关系的解决缺乏信心。在《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1937)中,Freud对完成分析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建议分析师每五年左右重新进行分析。Nina Coltart(1993)指出,我们的结束“非常奇怪”,我们的病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要结束?”"我们必须这么做吗?我们不能继续吗?为什么要结束一段如此有效、意义如此重大的关系呢?”
McClure随后向委员会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该结束了?我们怎么安排呢?我们怎么谈论它?结束有多绝对?“她请小组成员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谈他们如何处理终止的时间点,在某些情况下是否会逐渐减少,以及他们对分析后接触的看法。最后这个问题在培训分析中尤其重要,因为将会有某种持续的接触,但是人们希望将分析带向一个有意义的结束。
讨论小组成员对这个问题回答的清晰性意见不一。Alice Jones谈到了“一个正在酝酿的计划”。她说,理想情况下,结束的信号会从病人的材料中有机地浮现出来,一开始让人感到惊讶,然后觉得可能、可取、正确。
Mayer Subrin描述了一个分析的自然过程,以不同的阶段为特征,终止阶段是最后一个阶段。作出终止决定背后的驱动力,是分析师和病人都认识到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跌跌撞撞地走向终结”是一个经验,是整理出来哪些改变了,哪些没有改变,哪些还在期待,哪些应该保持不变的过程。在分析过程中,随着分析师逐渐消失在背景中,病人变得越来越活跃。死亡和重生的想象变得明显,病人为失去分析师而悲伤,同时也幻想着以各种方式留住分析师。为了说明这一点,Subrin从他自己的工作中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案例。通过这个例子,他证明了终止是如何在无意识中等同于死亡和重生的。
Jack Novick认为,当病人的选择能力恢复后,分析就可以结束了。在他的终止模式中,病人用一个新的系统取代了旧的封闭系统,旧的系统以全能幻想和施虐受虐为特征,而新系统的特征是与内在和外在的现实相协调,以及有能力、爱和创造力(Novick and Novick 2006)。Novick描述了准备终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准备好了讨论终止的工作,终止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一个新的说再见的机会,以一种新的、生命力增强的方式提出,病人和分析师一起探讨病人应对终止阶段的强烈的情感的能力。这是对终止工作的一个独特贡献,允许分析师帮助病人从僵持状态中走出来,或者检索受到过早终止分析的威胁。在这一阶段接近结束时,病人会选择一个结束的日期,有时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挣扎才会成功。
Glen Gabbard描述了这些年来他的想法的演变,以及在他的训练生涯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神话,尤其是关于终止的神话。这一神话的特征是线性模式:开始阶段、中间阶段、终止阶段。还有一个神话是完美分析的分析师,这就引出了完美的病人的神话。关于如何处理这种终止,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公式。例如:如果病人仍然有症状,那么终止治疗就为时过早;或者是由病人首先提出终止时,那将是一种阻抗,应该被忽略;或终止过程应该持续每年一个月的分析。
也有人认为这种移情应该得到解决。但终止后的随访研究表明,这种移情从未消失,实际上,当病人再次与分析师接触时,这种移情会立即重新建立起来(Pfeffer现象)。Gabbard指出,所有这些神话都涉及到一个典型的神经症病人。正如Harold Searles曾经说过的,“找到三个神经症病人就像找到三只雪豹”(Glen Gabbard,个人交流)。此外,在终止的模型中,分析师和病人就何时结束达成一致实际上并不常见。
实际上,终止对分析师的技术提出了挑战。如果分析师认为病人想要终止的愿望是一种需要分析的阻抗,那么病人可能会被迫留下来以满足分析师的愿望。虽然理想的终止是合作的,但事实上,在治疗接近尾声时,分析师的目标和病人的目标之间往往会出现冲突。在这方面,如果在分析过程的早期就讨论目标,这样就可以一起检查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差异,这是有帮助的。
Gabbard接着说,某些病人可能需要从他们认为的分析链中解放出来,以对抗他们所经历的强制治疗。如果分析师坚持认为病人必须留下来,病人可能会假装服从,同时暗自怨恨。然而,如果分析师为回归铺平了道路,病人可能会在需要时感到舒适。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有些人会在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好之前离开,但他们会回来,我们会做更多的工作。
最后,Gabbard指出,现实往往与理想相冲突,我们必须接受,生活环境将是决定终止的关键。Freud(1937)在《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一书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无论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态度如何,我认为,分析的终止是一个实践问题”(249页)。病人或分析师可能会被要求离开,财务状况可能会急剧变化,疾病可能会打击分析的任何一方。
Novick在这里提到了一种儿童分析技术,把分析师认为不符合分析实际目标的结果称为“暂停”。这是避免战争的一种方式,并允许在需要时返回治疗。
对于在分析结束时逐渐减少分析频率,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一些发言者认为,减少或允许病人在终止后返回进行更多的分析将干扰哀悼过程和巩固分析成果,因此对病人是一种伤害,尽管它看起来似乎是有益的。另一些人认为,有许多病人根本无法忍受突然的结束,需要更渐进的治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无限期的治疗。Henry Friedman在会议上表示,有些人并不打算终止工作,因为分析师一直是他们的支持对象,而他们尚未成功地与另一个人建立起支持关系。
Jones吃惊的注意到Nina Coltart的观点,在她的《关于结束》(1993)一章中说,她会让门微微开着,说如果出现什么情况,病人可以再来几次,但事先会设定时间限制。但是Coltart绝对认为这干扰了哀悼,在她看来,哀悼是单独进行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对丧失的否认。Jones补充说,许多病人都幻想着以一种避免痛苦、丧失和哀悼的方式去终止。虽然有些可以突然终止,但其他的,尤其是那些有早期丧失经验的人,可能需要以可容忍的速度逐渐减少。此外,一些病人需要对未来分析师的去向有一个具体的想法,比如在办公室搬迁时需要一张地图。
在机构中,哀悼分析师的丧失显然要复杂得多,因为在会议上与培训分析师接触是常有的事。Jones谈到了一位同事,他觉得自己从未真正终止过工作,因为他的分析师参加了大量会议,这确保了他会继续与分析师接触。然后,当他的分析师去世时,他感到措手不及。由于从未有过正式的告别,他觉得自己在结束分析的十年后,只能独自完成终止分析。
Glen Gabbard说,从他在世界各地的谈话来看,断断续续的分析并不罕见。当病人在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好之前离开时,我们必须为他们的返回铺平道路,因为有很多的病人确实回来了。丹佛的一项研究表明,70%的病人在分析成功后的头两三年内会联系他们的分析师。因此,在结束分析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病人返回的可能性,根据病人的个人需要调整终止。Gabbard补充说,这是在终止后保持分析界限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与以前的病人建立联系的一个原因,就好像他们可能会回来接受进一步治疗一样。
Gabbard指出,病人通常会在终止治疗后几天、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他所说的“终止治疗后的间歇性分析,为旧的内摄涂上新漆”。
他让我们想起了Freud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引用了《分析的可终止性和永无休止》(1937)中的一句话:“分析的任务是为自我的功能争取最佳的心理条件;这样它就完成了任务”(第250页)。Gabbard指出,没有理由去相信,在病人生命的某个阶段,经过特定年限的分析,就可以达到这些条件。因此,病人可能需要定期回来继续这项工作,为自我分析建立必要的条件。“而且,”Gabbard补充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分析师也应该接受定期治疗。”
Gabbard说,他认为有些病人确实需要逐渐减少。如果允许他们降低频率,最终一个月一次或每两个月一次,有些人会做得更好。有些病人只能这样做,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模型。
在小组这一节之后的一般性讨论中,一位发言者表达了一些听众对这种逐渐结束的方式的不安。他指出,丧失是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看似实用且有帮助的做法,实际上是低估病人。不给他们充分的机会来处理终止所带来的丧失,实际上可能会亏待病人,并剥夺他或她成长的机会。
随着终止的到来,病人和分析师都经历了哀悼和丧失。Theodore Jacobs在发言中评论说,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中,终止是最重要的反移情反应的沃土。
反移情在这个领域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出现,我们需要意识到并不断思考。我们早期的生活经历、我们一生中自己的结局,以及我们自己的分析的结局,都会影响我们对如何结束与病人的关系的思考。我们都对某些病人感到厌倦,而对另一些人,我们永远都不想说再见。有时,消极和憎恨的纽带比爱的纽带更能把病人和分析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有必要认真思考我们自己的结局,因为当我们考虑病人的结局时,这些结局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演。对于一些病人,我们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对于另一些病人,我们找到了结束的理由。这是我们工作中如此困难的一部分,因此,在考虑终止工作时,与一位能够以更中立的态度看待这件事以及是否该结束工作的同事讨论这件事尤为重要。
一些小组成员评论说,终止对分析师和病人都是一种丧失。Novick说,实际上,分析师的丧失可能比病人更大,因为病人对分析师了解甚少,而分析师却对病人了解甚多。对于分析师来说,结束这本书就像是放下了《战争与和平》(Warand Peace):读完这本书后,我们会感到悲伤,想拿起它从头再来。这是我们和某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生活,现在他们走了。
此外,Novick继续说,由于保密的要求,分析师必须独自为病人哀悼,没有其他类型的哀悼所能提供的支持社会结构的帮助。例如,对于一个人的死亡,有一个共同的公共悼念仪式,而对于分析的终止,分析师会遭受一个潜在的痛苦的丧失,而没有任何仪式。除了和同事讨论这个案例,没有任何场合可以表达失落感,也没有社会认可的仪式来承认这种丧失。哀悼是终止的一个重要部分,有终止阶段的一个原因是对它的存在的允许。哀悼可以内化分析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经验,巩固分析工作中实现的“开放系统”模式的自我调节模式。然而哀悼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病人和分析师都抵制哀悼:因此“准备终止阶段”,对确定两个人都准备好接受一段时间的哀悼期是很重要的。
Novick认为,在社会孤立的背景下,分析师痛苦的丧失感会导致他或她的反应是紧紧抓住病人,导致无终止的分析。在终止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严重的侵犯边界行为。随着终止的临近,变化常常发生在持续的分析立场上,即分析师通常行为的变化。某种关于终止的事情使我们所有人的行为都不同,有时我们完全失去了我们的分析能力。我们强烈建议,在与病人进行结束时,分析师可以与可信任的同事会谈此事。
Jones补充说,终止对病人和分析师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丧失。分析师正努力涵容双方的经验,并完成分析的基本工作,即拥有经验,然后将其转化为语言。她指出,在这个哀悼和丧失的时刻,也有一些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但双方都很难知道什么是破坏性的,什么是有创造力的。
在分析终止阶段的反移情会导致分析师违反边界和其他类型的设置。在这方面,Novick注意到精神分析的强迫终止史,从Freud单方面终止狼人分析开始。这一举动被证明是一场治疗的灾难,狼人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分析中,直到他死亡的时候都需要英雄般的措施来支持他。Novick指出了一种分析错误的连锁反应,从这种单方面终止开始。Freud与狼人的关系结束得太突然了,接着又过早地与Helene Deutsch的关系结束,为狼人回到他的分析中腾出空间。接着Deutsch突然结束了她和Margaret Mahler的分析,告诉她,她是不可分析的。Mahler的反应是与August Aichhorn进行分析,并迅速与他开始了一段风流韵事。Ruth Mack Brunswick,狼人的分析师之一,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他没完没了的分析中,被迫终止是一个因素。此外,Brunswick在暑假前的最后一天毫无预警地终止了Muriel Gardiner的分析。Gardiner在宣布自己很高兴的时候,接着表达了之后多年的深深的伤害。
Freud(1913)曾将精神分析比作一盘国际象棋。Novick采用了这个类比,他指出,在国际象棋中,一个好的结局可以使比赛免于平局,而一个糟糕的结局可以使一场真正好的比赛失败。同样,一个好的告别可以避免僵局,一个糟糕的结局可以毁掉一个好的分析。Novick强调了保持分析到最后的重要性。他要求病人为最后一个小时设定一个日期,注意到这个日期对病人经常有其他的意义,这掩盖了它是分析的最后一个小时的独特意义。设定一个日期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因为它标志着分析的中间阶段的结束,以及分析的永恒感。在这一点上,在旧的无所不能的运作方式和进入新的运作方式的恐惧之间存在着一场战斗。有时,病人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退行,以至于分析师开始怀疑按计划进行终止的明智性。
随着终止日期的临近,Novick建议对病人关于最后一小时的想法保持敏感。这样做的原因是,病人经常会计划带礼物或举行一个闭幕式,可能会有食物或音乐。这样,交流的方式就会从言语转变为行为,而在行动中就会失去安全感。此外,他还把病人的出其不意看作是旧的万能功能系统的一部分。Novick分析了病人对行为的偏好。他指出病人会记住他的话。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会告诉病人,如果他在脑子里再也听不到分析师的话,也许是时候重新开始分析了。
Gabbard发现在最后一天之前谈论病人对最后一次治疗的想象并尽可能地分析这些幻想是很有用的。但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分析师必须劝阻病人不要通过送礼物或拥抱分析师道别等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Gabbard指出,对许多病人来说,能够给分析师一份礼物是很重要的,这既是一种感激的表达,也是一种他或她能够给分析师一些回报的感觉。他指出,在最后一个小时内,分析师对病人的行为没有多少控制权,在这里,分析师应该让病人以他或她需要的方式结束。
Jones补充说,即使分析师询问病人对最后一小时的幻想,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意外。而这些自发的行为创造了持久的经验(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使得病人和分析师在分析完成时能够留在彼此的脑海中。Nancy Kulish补充道,有一个神话认为,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被分析,但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却无法分析给予我们的每一份礼物的意义。Gabbard同意,上一个小节的部分问题在于,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人们想要分析的一切。
病人送礼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需要被记住。Novick指出,我们的许多病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的父母无法看到他们的真实身份,也就是他和Léon Wurmser所说的“灵魂盲”。“因为这些病人被投射和外化以扭曲的方式看待,他们非常需要被他们的分析师以一种反映他们真实身份的新方式看待和记忆。”他们担心我们也将无法正确地记住他们。在分析结束时,病人需要给分析师一个礼物,这可能是一种需要准确记忆的表达。Novick强调,这份礼物不应该被拒绝,但分析师确实有责任,一直到最后,都用言语表达无法言表的感受。可能去说“我将永远把你和我们的工作放在心中”就足够了。
Gabbard同意许多病人担心他们在终止工作后不会被分析师记住,有时礼物的意义是确保分析师不会忘记他们。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知道分析师会把他记在心里,会把病人带在心里。需要被记住有多个决定因素。一个人与这种感觉有关,即没有被父母认识和看见,没有以他们真正的方式内化。病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被真正记住的机会,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这是一种弥补。赠送礼物还有其他含义;它可以是一种自恋的延伸现象,也可以是虚假自我顺从的例子。
还有一种存在主义的主题包含在需要被记住。我们通常认为永生是在死后被记住,而死亡的主题经常与终止的体验交织在一起。也有人希望否认这种“死亡”,通过赠送一份礼物,让病人永远与分析师在一起,永不分离,象征性地与分析师永远生活在一起。
此外,病人的被记住的需求,也与分析终止之后,分析师在这个时间要与哪个病人工作有关。
Gabbard让我们想起了Freud在1915年发表的《移情-爱》论文中所说的话:“分析师必须追求的道路……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模型的道路”(166页)。同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终止后阶段的模型。就像Coltart说的,在见了一个人很长时间后突然停止是很奇怪的,我们并不真正知道结束后的阶段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这方面很难提出明确的指导。
分析师有很多病人,但是病人只有一个分析师。这常常使病人产生这样的幻想,即他们正在与分析师的所有其他患者竞争。他们的理由是,尽管分析师是他们的最爱,但他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分析师心目中的位置。他们是最受欢迎的吗?他们怎样才能赶上班上其他同学?他们需要知道分析师对他们的高度评价,并在某种程度上确认这一点。
Novick在礼物上增加了一个历史性的注解。Freud告诉“狼人”,作为一种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病人送分析师礼物是件好事。作为回应,狼人给了Freud一件来自埃及的古器物,Freud在他的诊疗室里显著地展示了这件古器物。在Freud的办公室里,他的特殊地位意味着他在Freud心中的特殊地位。
小组结束时,Jones思考了我们结束的原因。在分析工作的最后,神奇的思考减少了,人们对现实的接受程度提高了。她说,最后一步只会出现在现实的领域,而不是想象的领域。死亡必须是真实的,生命才能以真实的方式存在。放手,经历丧失,真实地承受它,生活才能以真实的方式进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第一次放手的能力和忍受一切痛苦的能力。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双方的认可会提高每个人的能力,并发展病人的创造力,帮助他或她度过这一刻并结束。接受现实包括放弃永生和神奇的思考,生活在现实中,从而变得更加完整的人。
—————————————
2007年6月22日,在美国丹佛举行的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春季会议。小组成员:Mary Margaret McClure(主席),Glenn Gabbard, Alice Jones, Jack Novick, Mayer Subrin。
References
Coltart, N. (1993).Endings. In The Baby and the Bathwater.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 Press, 1996, pp. 141-154. - 1194
Freud, S. (1913). Onbeginning the treatment. Standard Edition 12:123-144. Freud, S.(1915).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Standard Edition12:157-172. Freud, S. (1937).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Standard Edition 23:209-253. Novick, J., & Novick, K. (2006).Good Goodbyes: Knowing How to End in Psychotherapy andPsychoanalysis. New York: Aronson.
(2009).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7(5):1185-1195
内容版权归原创作者和译者所有,转载本文需经过作者/译者同意,转载时禁止修改原文,并且必须注明来自作者/译者及附上原文链接。